
欧宁:你1957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64年迁往美国,在美国受的教育,我想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诗歌与文学感兴趣的?
欧宁:你记得你第一次写诗的时候是哪一年吗?
李立扬:第一首诗在高中的时候,是写给我妻子的情诗,那时候我们都是高三学生。但我一直到大学最后一年前,其实没有认真开始写作。那些诗歌都比较糟糕。
欧宁:你出版第一本诗集《玫瑰》(Rose)的时候是1986年,里面我们能看到很多你父亲李国元的影子,我看到有些中国学者写的论文也论述了这一点。我认为你父亲对你的写作有非常大的影响。你能详细谈谈这些影响吗?
李立扬:我觉得这很复杂。里面有很多层面上的影响。比如,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虽然已经是1960年代,我不觉得这个国家对亚洲文化非常了解,所以,对亚洲男性来说,塑造一种男子气概很重要。我父亲是个非常有力量、非常有男子气概的人,而他又非常中国。我觉得我与他的关系很深切,因为他总是能够传递给我双重的身份:男人的身份和中国人的身份。他觉得,他对男子气概的理解来自《易经》。我现在正在研究《易经》,想知道他对男子气概的理解。他认为男子气概是一种有创造力的、世代相传的、往前推进的东西。对我来说,在那个时候接触到这些想法非常有必要。但与此同时,他的男子气概又太强大,太过于有力量了,它让我害怕,有点压迫性和统治性。我也有儿子,所以我把这种教育方式也继承了一些,我想大概家族的传统就是这样传承下去的,包括这种对男子气概的理解。
欧宁:你的父母对你是典型的严父慈母,你父亲对你挺严厉,你妈妈对你比较慈爱,我从你的一些诗歌里面和你的那本回忆录《带翼的种子》(The Winged Seed)可以看出来。你父亲对你的影响,刚才你已经说了,那你妈妈袁家英给你的影响具体又是怎样的?
李立扬:我母亲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她的性格非常宽宏大量,我觉得她看得清楚所有事情,她不经常介入,但她仍然很有影响力。她对各种礼节有深刻的理解,她把这种东西教给了我们。我很小的时候就在美国长大,但我们从来不与她说英语,我们只说汉语,也因此,我还会说那么一点点的中文。如果不是她的话,我连一点中文都不会说。所以,她身上有种力量。我与她那一代人有很多交往,那一代的中国人经常鼓励自己的孩子完全融入美国社会,只说英语,不说中文。但我母亲抵抗这种想法,我非常欣赏她的选择。她有种天然的能量,热爱礼节。她有种气场,所有的孙子孙女们在她面前都能表现得很有礼貌,很亲切,且很有爱,他们表现出来的礼貌很美。我非常敬仰这一点,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把孩子们身上的礼节性给带出来的。她也非常宽容,能够允许很多事情,很开放,我尝试从她身上学到这些东西。
欧宁:你在写那本《带翼的种子》之前去过中国?你是不是只去过一次中国,与你母亲两人去的?
李立扬:不是我们两个,我与我母亲,我的两个儿子,我的哥哥、姐姐,整个家庭都去了。
欧宁:这是不是你第一次回中国大陆去寻祖?
李立扬:我很坦白的说,我其实不想回去。我人生的大部分在北美度过,我有种强烈的无家可归感。我在这里并不舒服,我不觉得这里是我的家。我总觉得有一天,我回到中国,会有家的感觉。但我自己也知道,这不是事实。所以只要我不回去,我至少有种幻想,那里的某个地方有我的家。我很害怕,如果我回去了,我会发现我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我什么也不是。但我想如果我永远不回去,我总可以想我是中国人,我不属于这里,不属于美国。但我回去以后,我的很多中国表兄弟姐妹们跟我说,你不是中国人,你的行为举止不中国。他们看我洗脸的样子,说我都不像中国人一样洗脸。所以我想,好吧,我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所以我不应该回来。只要我不回来,我总能相信这里是我的家。但现在我的无家可归感变得精神化了。我不觉得我在整个地球上有故乡。我只不过存在于这个地球上,但我不适应它,我没有家的感觉。
欧宁:你是不是去北京拜祭你祖父李肃然的墓了?然后你也去了河南安阳袁世凯的陵园?在这个寻祖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找到一种对家族或者中国的认同感?
李立扬:我觉得我有,但他们一直跟我说,你不是中国人,你走路的样子不像中国人。我想找到身份认同,但我的表兄弟和大多数其他人都告诉我我不像。我感到自己是个中国人。一个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你觉得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这么认为。
欧宁:我觉得你很像中国人。
李立扬:我也觉得。
欧宁:你的写作中有很多中国的文化,非常深刻的东西,你不像典型的美国人。
李立扬:很有趣。我与很多华裔诗人交流过,他们告诉我我的作品不够“华裔”,但我感到我的作品比他们更中国。哲学是中国的,态度是中国的,设想是中国的,形式上也是中国的。我像个年迈的道家诗人。我不觉得我是个美国诗人。虽然我是个美国公民,我觉得我非常中国。
欧宁:你的写作当中有强烈的中国家庭伦理观。
李立扬:是,我希望我能传递这样的东西。我的孩子,我培养他们的时候用的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教育观,要尊敬老人,把老人永远放在你自己之前,所有这些,都是很古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现在在中国还有吗?没有了吧?
欧宁:今天我到这里拜访了你家,发现你家几代人都住在一起。这在中国已经很少了。每个孩子长大以后,结了婚,就会搬走,把父母留在乡下。我想你的价值观放在当代中国也算很传统的。你能再讲讲你在中国的经历吗?你也去了苏州和其它几个城市?
李立扬:我很喜欢苏州和杭州,我的问题是我有点幽闭恐惧症,我不喜欢旁边有太多的人。我会感到焦虑。中国很拥挤,有时候对我有点困难。我很喜欢天津,喜欢那里人说话的口音,我也很喜欢在他们那里看到我自己的脸,好像照镜子一样,马路上有很多与我相近的脸。我对中国之行有很好的记忆,虽然也很感伤,因为总有人对我说你是从美国来的。现在去的话也许会不一样了,也许我能更好得融入其中。但我上次去的时候是1989年。也许现在还是很不一样。那个时候我真的能在人群当中跳出来。我不喜欢这样。不过我很喜欢中国,虽然在那个时候,古老的中国,我母亲的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母亲很难过,我与我母亲关系很亲密,所以她的难过我也影响了我。这是对逝去的中国的难过,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中国。

[李立扬的母亲袁家英(前排)与他的外祖父袁克桓(袁世凯六公子,后排右)及外祖母陈征(后排左),网络图片]
欧宁:所以那次旅行是《带翼的种子》这本书的源起?你能告诉我你是怎样写这本书的吗?我听说这本书明年会加印?
李立扬:这本书有很多问题。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觉得最诚实的写作方式是不加修改的。这很愚蠢,但这是任何年轻作者的妄想。里面有种佛教的想法——第一个想法是最好的想法。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是这样,我买了个手提电脑和Word软件,把屏幕关掉,这样整个屏幕是黑的,然后我打字,这样我一边打,一边根本看不到我写的东西。很可怕的写作方法。很奇怪,对吧?我用笔写作的时候总是觉得一边写一边感到十分的累。但我在打字的时候,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屏幕是黑的,我根本看不到我写了什么。我会每天都写,从来不读。大概三年以后,我把文件放到了一起,交给了编辑。所以我重看这本书的时候,意识到这根本是一团乱麻,你必须修订。我不觉得艺术是喷泻的结果。你必须选择,重写,知道怎样组织更好的句子,更好的意象,但这本书就是这么回事……我几乎不敢看它。每次我看这本书的时候都意识到这是个灾难,一场失败。有些人告诉我他们喜欢这本书,所以我……我现在在修订它。但我15年来从未动过它。我依然想要原著里的那种兴奋,但我也想给予它一些其它东西。我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
欧宁:什么时候会出版?
李立扬:再版的时候不会是修订版——我还没修订完。再版,就是明年十月的时候,会是一样的版本,只是重印而已。
欧宁:除了这本书和《玫瑰》之外,你还出版了另三本诗集,1990年的《在我爱你的那座城市》(The City in Which I Love You),2001年的《我的夜晚之书》(Book of My Nights)和2008年的《在我眼后》(Behind My Eyes),你能告诉我每本书的主题有什么不同吗?
李立扬:我很抱歉的说,我的写作只有两个主题,永远在重复同样的主题:死亡与爱情。我的想象力并不出色,总是这两件事,我脑子里只有这两个主题。我起床的时候在想这两件事,我上床的时候还在想这两件事。我的梦里只有爱情与死亡,所以我是个非常有局限性的人。总是一样的主题。
欧宁:你的文学影响从哪里来?你最喜欢的诗人是谁?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李立扬:我不知道。我知道《旧约》和《圣经》对我很重要。我不认为我本性是个基督徒,我不清楚,但《旧约》里的一些想法对我很重要。最大的影响可能是道教。道教对我父亲很重要,他给我们念过很多《道德经》和《易经》,他给我们念《易经》的时候不是当作算命书来念的,而是哲学书。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这两本书,它们非常深,我并不完全理解,但我觉得我受它们影响非常之深。
我的写作中所有的形而上学基本都是道家的,比如道家认为世界从语言和词语而来。这对我很重要。也有一些美国诗人、英国诗人、南美诗人和西班牙诗人我很喜欢,但对我来说,我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是道家的看法。
欧宁:如果我们不说哪些诗人对你影响比较大,只是让你推荐几个北美诗人给中国读者,或者给《天南》翻译成中文的话,你有什么推荐?
李立扬: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enson)的诗歌非常深刻,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有些诗歌也是,像海洋一样深,深不见底。还有费德里克·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也是个非常深刻的诗人。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也很深刻。《中国歌谣集》也很不错。我也很喜欢莎士比亚,可以一直一遍一遍读莎士比亚。
欧宁:你的家族和政治有源远流长的关系,你曾外祖父是袁世凯,你父亲李国元,我在网上也找不到不少关于他的故事。
李立扬:你知道,有过一部电影,里面有我父亲和毛泽东的故事。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在美国,五年级,我们看了一部历史电影,里面有架飞机降落,门打开,毛走下舷梯,我父亲也在走下舷梯,两人在一起。我坐在学校里,我想,这是我父亲啊,当然,班里没人知道,我回家告诉了我父亲。我说我在一个电影里看见你了。他什么也没说。我反复问他,他才说,我曾经与毛关系很近。他给我看了一些照片之类的。我的家庭……他们在政治上的经历并不愉快,他们不愿意多说这些事。我知道的也不多。
欧宁:所以迄今为止你也不太了解?
李立扬:我不太了解。老实说,我的家庭承受了太多政治苦难。我父亲去了印度尼西亚。我们在那里……他在那里呆了两年,然后我出生了,苏卡诺,当时的印尼总统开始屠杀中国人,监禁中国人。我父亲坐过牢。他经历了很多政治动乱。我个人的感觉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我只对灵魂上的变化有兴趣。我不相信政治变化是可能的。我不相信世界会因为政治变得更好。我真的不相信。我觉得如果人们能够在心理上、精神上、灵魂上发生变化,世界才会变得更好。我觉得有两件事同时在发生,一个灵魂进化,或者说对于地球的看法趋向更为灵魂化的认识的进化。但表面上,总是有些政治上的东西,我们觉得这些事跟政治有关,其实它们跟政治无关。所以我对政治没有兴趣。我知道在我母亲那边,因为与袁世凯的关系,也有过一些政治上的风波,但我真的没有兴趣。
欧宁:你读报纸、看电视多吗?
李立扬:我看电视只看电影。我对新闻没兴趣。因为都是谎言,经过选择的谎言,即使在美国也一样。这里没有逐字逐句的审查,但有其它形式的。
欧宁:你关心中国现在这些新的发展吗?在今天来说,中国对你意味着什么?
李立扬:我内心的中国是我父母对我讲的中国,旧中国。现在我听到有关中国的事,我觉得很难过。我有种感觉,现在的中国物质主义很猖狂,这对我来说是件让人很难过的事情。我觉得如果道家思想是人类精神认识的高峰,我不知道如此高妙的思想是怎样完全被遗忘的。这个国家走向了完全的反面,完全没有精神认识的那一面。对数量的崇拜现在在中国盛行,不是吗?用金钱来衡量所有东西,但我们应该知道,金钱能衡量价格,却不能衡量价值。现在的一切都有关价格,而非价值。这让我担忧,让我心碎。因为我觉得很少有其它文化能够到达道家的那种境界,中国达到过,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听到当今中国的事情的时候,确实感到很难过。
欧宁: 你说你曾经想回去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住呀什么的。你现在还有这个想法吗?
李立扬:有,我很想。很多从中国来的人跟我说,立扬你没法在那里生活,你没法适应那个环境。但你告诉我我可以。也许我会试试看。我很感激美国,这个国家接纳了我的家庭,当我们是政治难民的时候。但在这里我感到非常疏离,非常边缘,很多这里的价值观我无法接受。我不知道。也许我回到中国,会发现我也不能适应。但我有时还是会想这事情。
欧宁: 很多研究文学的人,经常把你的诗歌和写作归在“亚美文学”(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这个概念里面,这个概念很强调移民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参与,移民的文学其实也是美国文学的一部分。我发现你的民族观念很强,你的中国感情也很强烈,跟新一代的移民作家例如李翊云相反。她很强调自己不是华裔作家,对国家和民族的界定很淡漠,你觉得我说的准确吗?你是不是这样,可能是因为你的年龄比他大,还有你家族的特殊原因,我觉得你有很强的乡愁,包括回去中国的那种意愿?
李立扬:也许因为,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年纪很小,当时这个国家对东方非常无知。所有我遇到的人都说,中国没有文化,没有文明,所以我的反应是走到另一面去。我上高中的时候曾经一直穿中国服装去上学,棉袄、高领子,中式衣服。我会自己带午饭和筷子。因此,我总是在与周遭斗争。我是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很小的小镇上上的学,那个时候美国在和越南打仗,一个亚洲国家。那里的人分不清楚越南和中国,对他们来说都一样,所以他们讨厌你。针对我的那些仇恨,对我从心理上来说是很复杂的。一方面,针对我们的仇恨和种族歧视让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有反抗性,我们拥抱自己是中国人的事实,喜欢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想法。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吸取了一些自我的仇恨。这很复杂,并不是个快乐的氛围。如果一个中国人在中国长大,也许他们对自己的中国性有更强的安全感,而如果在这里长大,你必须斗争才能做个中国人,或者说,保持自己的中国性。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遇到的很多中国人不跟我说中文。我会跟他们说中文,他们会假装不说中文。我有些中国表亲会装作他们从来没吃过中餐。我们有时去中餐馆,我的中国表亲会说“我不吃中餐”,所以这种反亚洲、反中国的感情很强烈,因为那时的越南战争。也许我们很疯狂,有些反对主义者的感觉,我和我弟弟妹妹决定我们只吃中餐,只穿中国服装,所以我们当时的生活非常奇特。当然我们活下来了,所以有时候,现在,在北美,有很多诗人说他们喜欢佛教,喜欢道教,我看着他们,我真的非常讨厌。因为他们太假了,他们在误读佛教,误解道教,完完全全的误读与误解。所以我对此有很复杂的感情。我真的觉得道学孕育了这个世界,而佛教,如果正确理解的话,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不过我不知道。很复杂。坦白说,过去几年内,我发现了自我仇恨这样东西。我以前从来没感到自我仇恨,但我现在觉得我身上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不知从哪来的,也许从外界来的,我被吸收进去了,也可能是中国家庭教育子女的方式。我父母是传统家庭长大的,他们爱孩子,孩子很重要,但孩子在一个传统中国家庭里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欧宁:你说的在你的某些诗歌里也表达过。这种中国的身份在美国的日常生活里面,学校里面,这些故事,发生的这些冲突我都有在你的诗歌里面看见过,所以我才会这样问你。接下来的问题是,你一直生活在美国,你说你也不太爱旅行,有可能我猜想你跟华语文学,包括台湾香港大陆这些用中文写作的诗人、作家的交流都有可能发生在美国本土,这些人来美国会见到你。我想问问你,你跟整个华语文学的交流是怎样的呢,你认识谁,见过什么样的大陆诗人,台湾、香港的作家,请讲一讲你跟中文作家的交往。
李立扬:你知道吗,因为我有一点笨,我与别的作家见面的时候,我曾经很兴奋,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不喜欢了。你与一个作家见面的时候不是在与一个人见面,而是在与一个作家见面。我见过北岛,我不知道北岛是谁,我见了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作家北岛,但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知道他的梦是什么颜色的,我不知道他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我不知道他更喜欢哪条围巾,我不认识这个人。我见过乔瑟夫·布罗斯基( Joseph Brodsky),俄国诗人,我见了那个著名诗人,但我没有见到乔瑟夫·布罗斯基,那个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这是件毫无希望的事情。你见到的永远都不是人,而是他们头上的光环。道家的理论里,一个人最大的成就是做一个头上没有光环的人。但每次你见一个作家,只有光环,没有人。我不知道,这让我难过。我有些朋友成为了著名的诗人,但他们变成了他们头上的光环,我认不出他们了。也许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喜欢待在家里,我母亲总是叫我小混蛋,只要我在家,我总是小混蛋。我知道我是小混蛋。但出了门,我成了著名诗人,但我不是,我是小混蛋,我是我儿子的父亲,我妻子的丈夫。而除去这些身份之外,我还是比“著名诗人”四个字更丰富的人。我也想交朋友,在美国当一个诗人是件非常孤独的事情。我很想交写作的朋友,但每次交朋友,你都是在跟他们的光环交朋友。我不想这么做。
欧宁:我感觉你还是一个比较喜欢呆在家里,比较孤独,自己写自己的东西的人,所以我想从阅读方面问你和中国文学的交流,虽然你不能读中文,但有一些中文作品,也曾被翻成英文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一些中文诗歌的英译?
李立扬:我读过,但是我要告诉你实话,我相信我没看过好的翻译,因为我看的,他们翻得很不好,所以我没碰到过一个好的翻译。英文总是不好,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我在这些翻译里看不到深刻的东西,我想也许是翻译不深刻。
我读诗歌的时候,如果是一首伟大的诗,我能感到有四个层次的自己同时在发声。一个公共的自己,好像现在正在跟你说话的我,公共的、社交的,这是一个层次。还有一个私人的层次,一个只有自己和他最亲密的家人才知道的自己。一个人公共的一面与私人的一面是不同的,对吧?但还有一些更深刻的东西,秘密的自我,一个我妻子、我儿子、我母亲和我兄弟都不知道的我。我有两个儿子,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们社交的一面,他们私人的一面,偶然的,有时候能看见他们秘密的自我,如果我能客观地分割我的感觉的话。但更深的一个层次是一个莫名的自己,连我也不知道的自己,无意识的自己。只有在读古代中国诗歌的时候,我才感到四个层次都在。世界上很少有诗歌,不管是美国的、英国的、西班牙的、翻译成英文的中文诗歌、德国的还是捷克的,很少有能让我同时感到这四个层面的诗歌。
欧宁:在《天南》文学双年刊的第三期里,我们把一些八十年代的中国诗人的诗翻译成了英文,我特别想咨询一下你的意见,看那些翻译得怎么样。有空请您看一下。多谢你今天抽空接待我的来访。谢谢!
*由赵婷根据录音整理,btr审校;俞冰夏从英文译成中文,经欧宁审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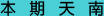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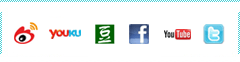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