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宁:作为一个作家,你觉得新疆有些什么样的资源能够提供给文学?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在新疆,我觉得最大的资源还是人文资源。新疆历史上就是一个人类足迹流通的、血脉流通的、文化流通的、经济流通的一个国际通道,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在新疆,有呼吸特别畅通的感觉。如果纵深地去说,就是你可以深入到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它们已经在这里给你提供了一些经验,比如说游牧文化、农耕文化,还有东西方文化,有很多具体的人和故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文化事件留下来,你纵深地去感觉的话,就会觉得非常丰富。包括宗教这一块,不同的宗教都在这里留下了痕迹,比如具体到哈萨克这个民族,在它以前的宗教价值观上有来自于它祖先的对生命世界、大自然的认识,对社群关系的认识,同时它也接触了很多外来的宗教,都有印记在里面,纵深地去看的话就有很多积淀在这里边。
从现实来讲,你横向地去比较,这里现在有47个民族,虽然47个民族的47种语言在这里不一定有很充分的展示,但至少有13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可以通过汉语的平台上构建,所以从认知和认同感来说,横向的交流还是存在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民族政策,在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方面,政府层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新疆现在共有11家文学杂志,新疆文联出版的就有五种文字的杂志,包括哈萨克语的《曙光》,维吾尔语的《塔里木》,柯尔克孜语的《柯尔克孜文学》,蒙语的《启明星》,汉语的《西部》。作为生活在本地的社群、民族,这五个不同语言的民族,本来就有很强的发展愿望,都在不断地努力,尤其是这二、三十年来,随着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的改变,对文化的支持力度加大,本民族和不同民族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展示愿望,这些你们到处走走都能感觉到。最突出的就是比如你到旅游区,具体说你到哈萨克的旅游毡房去,有很多民间图案都裱到毡房里头。
真的,从纵深的和横向的角度都是这样,就像我前面所说,呼吸还是很畅通的。这种人文资源给你提供的可能性很多,问题的关键是作家们具不具备这种洞察力和捕捉能力。如果发现了,能捕捉到,然后通过文字展现出来,它将不光是某一个民族的,而是人类共同能够接受的,我在《永生羊》这本书里想要达到的就是这种水平。我对哈萨克民族很熟悉,我的文化的载体就是哈萨克族,我的价值观一定要构建在大家都能接受的平台上。这个世界之所以丰富,就是因为这些不同的载体的存在。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一个人类共同的基础的价值观,比如爱父母、爱孩子、教育孩子健康成长、和睦相处,这是人类共同的东西。
欧宁:新疆47个民族里,有人口比较多的民族,像哈萨克,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还有自己的文字,1949年之后周恩来曾经组织过少数民族的识别工作,他发现有的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然后他就请一些专家去设计文字。在新疆有没有这样一些民族,它本来是没有文字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设计才有文字?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就我所知,这种情况基本上是没有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蒙古族,这五个民族,历史上一直有文字的延续。尤其是突厥语系的这几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经沿用过自己的语言文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沿用过拉丁字母,叫新文字,但后来因为普及方面的具体原因,现在又恢复到老文字了。有意识地去设计文字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
欧宁:你本人开始写作时是用哈萨克语还是用汉语?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汉语。在新疆我们有一个概念,叫“民考汉”,这个你知道吧?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这代人属于最早的受比较规范的汉语教育的一批人,从小学一年级甚至学前班开始,就有比较正规的汉语教育。在我们以前可能也有,但都是在中学阶段或是大学阶段,才有汉语的基础性教育,严格来讲叫扫盲。我们是属于比较正规的汉语教育,哈萨克语我是自己学的,我的父亲母亲都是老师,而且是哈萨克语的老师,在家里学的。
欧宁:在《永生羊》里边,你写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吧?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六十年代,我是六十年代出生的,1968年上的小学。
欧宁:在你的写作里边,除了汉语这个文学传统之外,你和哈萨克族的文学传统有没有传承关系?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太有了。在新疆这样多语种的地方,我们的精神世界、意识里头总是有一种母语和第二语言的概念,像我,我的母语就是哈萨克语,我在家里跟我的亲戚朋友讲哈萨克语,这都是天然传承的,就像说汉语的孩子背唐诗一样,我的知识构建,比如最朴素的民间哲学、谚语化的东西都是在血脉里头的,就像《永生羊》这篇作品里的一句“你死不为罪过,我生不为挨饿”。哈萨克是一个游牧民族,它的生活必然要和动物打交道,如果说农民秋天收获的是麦子的话,哈萨克族人收获的是动物,是牛羊,牛羊是活的生命,也是我生存所需要的食物,在结束一个动物生命的时候,哈萨克族人有这种很自然的表达,它的意思就是,“对不起,我需要你”,这种东西甚至不是宗教,它是一种生存方式。
小时候就听到“你死不为罪过,我生不为挨饿”,后来我自己也有家了,也需要冬宰,就像农民在收割庄稼要入库一样,游牧民族也要把一个冬天的冬肉储存起来,到了我成家立业以后那句话就脱口而出,这肯定不是来自于第二语言给你的认知。汉语对我来讲,汉语世界提供给我非常丰富的文学经验和知识积累,我在大学的时候,比如一个汉族同学读的唐诗宋词元清戏曲,还有后来的钱钟书这样的大家,汉语白话的美,它的节奏,这种东西会慢慢也进入了我的语言表达里边。
欧宁:我看《永生羊》这个散文集子里边《脐母》的那篇文章,哈萨克妇女的形象非常活灵活现,你在那篇文章里面也写到了传承,因为你后来也成为了别人的脐母。整本书给我的感觉,你写北塔山的牧道,写阿勒泰东部地区,写了一种完全未被任何现代化污染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你写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书上看来非常淳朴美好,现在你在乌鲁木齐生活,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愤怒或是不满?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有,怎么会没有。愤怒和不满太多了。我还写过一篇散文,叫《新娘》,其实写的也是那时候的北塔山,那个新娘整个婚礼非常混然天成的场面,我有句话,“这是我看到的最后的游牧生活的风景”,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比较成熟了,朋友说我怀旧,这种怀旧其实来自于对城市的愤怒。
我觉得十几年来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城市里到处都是铁栅栏,你走到马路上有很多护栏,在你家窗户外边有防盗窗,门也是防盗门,到处都是铁和网,抬头一看,脑袋顶上全是电线,你走着走着,说不定路上的井盖被某人以非正常方式拿走了,你总是提心吊胆。除此之外,在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眼睛后面还有一双眼睛,需要更多的设防。
现在城市生活节奏比较快,它是按分和秒来计算的,但我们过去的生活不是这样的,比如你去参加一个婚礼,是对这家主人的尊重,你会花时间准备,满怀情感,这些与分分秒秒和铁栅栏这样的东西是冲突的。有时候愤怒来自你自己,你不知道为什么适应不了这些东西;有些来自于你的朋友,他们可能也不适应。
欧宁:可是我在《新娘》这篇文字里面看不出你的愤怒啊。你是不想把你的愤怒写到你的文字里边吗?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我不想写愤怒,我的四、五本书基本上没有很恶的东西,比如《永生羊》这本书里一个也没有,我根据它改编的电影里边也是一个恶人都没有,不是我不想看到恶人,我想别人可能比我写恶写得更好。我的书里有很多爱情的主题。
欧宁:《永生羊》一书中更多的是写生命的主题,它在不同的时空中的转化。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对,《永生羊》想表达的就是生命的轮回,这个世界真正的主题是生命与时空。你回过头去看,这个地球上自从有生命以来,生命世界里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欧宁:我见过的很多作家都有很强的历史意识或者说文学史意识,如果把自己放在一个新疆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之下的话,你对自己的评价是怎样的?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有很多外来作家来写新疆,我阅读这些作品,但读着读着就发现有些东西,好像唱歌音调没有唱准那样,所以我也有种表达的冲动,也想来说说我感觉到的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疆。比如说我所有的文字里头,经常写到云,有一天我早晨起来,看见天上有片云像真的羽毛一样,巨大的羽毛,我就这样写,写完以后就觉得非常准确。小时候我听老人说过,新疆的风是一层一层刮的,如果是那样一层一层的话,云的形状肯定不像南方的云。我看到的是具象和意象中的新疆,意象中的新疆就是不同的民族在这里,对这块土地有不同的理解方式,比如对天山,维吾尔族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哈萨克族有自己的理解方式,我是从本民族的角度去理解新疆。如果说我们这种写作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本地人,我们自己写自己。
我的文字,我一写就有一种比较伤感、幽怨的感觉,找不到那样的感觉我就写不下去,“手拉手奔向美好的明天”这种我写不出来。哈萨克的民歌直达主题,比如爱情的主题、母亲的主题、故乡的主题,这三大主题基本上都是幽怨的。比如哈萨克民歌的爱情主题,因为游牧生活,不断的转场带给人心灵的一定是悲欢离合,路途的遥远、无能为力,一定就有种对大自然的无奈,这时候就需要歌声、诗歌去表达,就要用谚语去总结。这个东西在我的文字里头,我才能找到哈萨克的感觉。去年我出了本哈萨克民歌集,现在看来汉语系的读者对它的评价非常好,哈萨克族对它评价也非常好,因为我找到了一种合适的表达。其中有一首情歌,“爱人的毡房远了,看不见了,小鸟的脖子酸了,心都伤了”,就是说在毡房搬迁以后,仍在不断地看、不断地看,这种感觉,可能没有游牧生活经验的人是不会有的。
欧宁:刚才你也提到新疆的人文资源,如果从比较宽泛的角度来讲,新疆的人文资源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新疆在自身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建设上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新疆有一种精神气质,从总体上来讲非常大气,非常开放,我觉得这种东西要放大,放大了以后,东方和西方才能在这里找到一个对话的平台。这就是新疆文化的精神气质,有的时候它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有些地方有大型会演的话,不同服饰全部汇聚到舞台上来,这就是它的精神气质,每一个个体都有他(她)自己的色彩和个性。
欧宁:具体到某一种文艺形式呢?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现在宣传得比较多的是阿肯弹唱,“阿肯阿依特斯”实际上就是诗歌的对擂,它有传承和普及上的难度,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民族语言的诗歌对擂,所以从宣传和普及上比较难。还有一个更大的资源,就是新疆各民族的史诗,相当了不起。维吾尔族的史诗有72部,哈萨克族的有200多部,蒙古族也有100多部。哈萨克族的200多部史诗分两大类,第一类是英雄史诗,第二类是爱情史诗,而英雄和爱情的主题,永远是人类的主题,走到哪儿永远也不会被磨灭。
欧宁: 我们聊聊经济方面的话题,从你个人观察的角度来讲,这几年新疆,不仅仅是乌鲁木齐,也包括南疆北疆,还有一些偏远的地方,在经济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对这种变化你的评价如何?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变化肯定是有的。在五年、十年前,在乌鲁木齐定居工作的哈萨克人相比现在的人数来讲是少的,主要集中在新疆日报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还有电台、电视台、大学这样的部门,现在这几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哈族人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见,尤其是在服务行业,而在服务行业里年轻人的比重非常大。十年前我到桦林市场去基本见不到哈族人,现在基本上60%都是哈族青年。其他地区的餐饮业,哈族的服务员人数也非常多。还有在这里定居买房子的哈族人也多起来了,这些哈族人聚居的地方都给取了哈萨克名字,比如“双柳河”、“双峰驼”小区等,这在规划里是没有的,哈族人自己给自己的聚居区取名字,这就是非常大的变化。
前年拍电影《永生羊》的时候,我全程跟踪下来,参与制片、副导演、后期制作,我们要到山上去找比较淳朴的哈萨克族的毡房,很多基本上已经没了。现在牧民定居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游牧生产方式里的转场依然还是存在的,人们一直以为是动物跟着人转场,实际上是人跟着动物转场,到了夏天的时候一部分人还是要到山上去放牧,现在的放牧和以前的放牧完全是两码事,年轻人只要带着半个毡房上去就行了,所谓的半个毡房是简易毡房,只是个临时的概念,不是生活的概念。这种变化是非常深刻的。以前游牧惯了的牧民也开始一个适应定居生活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方方面面,包括邻里关系,包括对电器、煤气、灶具的适应,还有法律的建立和自我保护意识,诸如此类种种。
欧宁:在新疆,哈族跟汉族的冲突是不是会少一点?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从老百姓层面来讲,从生活上去看这个问题的话,小小的摩摩擦擦都是有的,小小的和和睦睦也是有的,这跟你在内地的一个楼里面住着的情况是一样的。彼此之间也都开些玩笑,都是很自然的。有可能我的汉族邻居不经意之间把我不能接受的一个什么东西放到我的门口,我觉得这不会上升到一个很原则的高度。从老百姓的生活上来讲我们希望政府给我们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让我们在这里生活,实际上就这么简单。
欧宁:作为一个作家,你的写作对象是本族人还是汉语系的人?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我的读者是汉语系的。我写过一本书叫《草原火母》,那个就是主要针对像我这种“民考汉”的,关于民族文化的内容。我们读的都是统一的课本,它不可能把你相关的民族知识放到教科书里边(现在的双语教育是例外),这种情况下很多关于自己本民族的知识就缺失了。当你工作了,等你是一个社会人的时候,尤其像我们这种从事文化工作的,很多人就会问起你,那我就要把这些课补上。《草原火母》就是针对“民考汉”的这一批读者写的。
欧宁:你的母语是哈萨克语,你作为一个哈萨克人用汉语写作,给我们这些阅读汉语的读者,这有点像哈金在美国用英语写作。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我觉得很自然。首先先决条件是我学的是汉语,再者就是前面我说的,很多人音准没有唱对。比如像哈萨克的《姑娘追》,以前的解释一直是说谈恋爱的,我小时候挺纳闷的,这种谈恋爱也太蹊跷了,后来我就觉得这种解释不准确,就一直在考证,去问一些年长的人,再通过发散性思维把分散的点联系起来,结果发现哈萨克的谚语里面有一种说法:闺女的娘家的福不是福,嫁出去以后的福才是真正的福。民间教育最大的本事就是用仪式的方式来告诉你,这样才有了《姑娘追》,所谓的姑娘追就是让你追上你的幸福。
欧宁:刚才你说游牧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跟以前不同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你对哈萨克文化有没有一种危机感?定居不仅改变了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生产方式,游牧文化可能会因为定居而慢慢消失,那么文化的差异性怎么保存呢?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我觉得这是历史的必然。相比较而言吧,比如哈萨克斯坦,统一语言、统一文化的这样一个跨国民族,哈萨克斯坦早就已经国际化了,他们的游牧方式、生产方式在前苏联就已经和新西兰那样的国家一样了,他们是以合作的形式进行游牧的,也就是说在一百年以前就已经没有了。相对来讲,在中国的哈萨克、蒙古国的哈萨克还保持着。改变是历史的必然,谁也没有办法阻止它。作为文化和精神的传承的话,就需要人为的保护,哪怕是用演绎和表演的方式。
欧宁:那些牧民对于政府鼓励他们定居的态度是怎样的?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我以前也采访过,他们说只要你给我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我也巴不得定下来,因为现在整个现代化渗入人们的生活太紧密,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所谓的牧民不愿意定居下来,道理非常简单,到夏天的时候,动物在平地上待不住,热得很,到处都是苍蝇,在高山上雨水充沛气候适宜,又是一个休闲的地方,你把人家避暑的时间剥夺走了,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不是毡房的生活多么牧歌情调,那还是作家和诗人眼里的事情。是我们把问题看得太复杂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很简单、很自然,但是因为条件不允许才很艰苦。我也采访过这样一个牧民,他把羊看成浑身是毛的敌人,我问你为什么说它是敌人,他说,你想想夏牧场,白天把羔羊群放在这边一座山上,母羊群放到那边一座山上,归牧的时候就要撒盐,动物要吃盐,你看那些羊恨不得把主人吃掉,它们要抢,你不能给得太多,要按他们身体能承受的量来给,动物不知道,拼命地吃,你就要打它,人和动物好像是一个对立的关系,所以他把羊叫长着毛的敌人。
欧宁:在内地,传统和现代化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对农村地区的挤压,这样的冲突在新疆是一样的吗?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我觉得本质上是一样的。城市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城市人往农村跑,占用别人的土地、别人的空间,然后农村人就和你对着干。
( 2012年8月9日,上海2666图书馆周焰根据录音整理,经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和欧宁审校。今日美术馆“刘小东在和田“艺术项目新疆采访之一,其它被 采访的作家包括李娟、刘亮程、董立勃等。本项目由侯瀚如和欧宁联合策划。官方网站:www.hotanproject.or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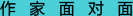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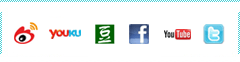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