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上的一切都以“是的”开始。一个分子向另一个分子说了一声“是的”,生命就此诞生。但是前史之前存在着前史的前史,有一声“从未”,有一声“是的”。永远有这些。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宇宙永远不曾开始。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藉由很多努力,我才拥有了简单。
只要我有疑问而又没有答案,我都会继续写作。如果前前史之前已有神秘怪物的存在?如果这段历史不存在,将来会存在。如果一切在发生前发生,那又如何在开始时开始?思考是一种行动,感觉是一个事实。两者的结合——就是我写下我正在写的东西。上帝是世界。真实永远是一种内在的无法解释的接触。我最真实的生命不可辨认,它是极端的内在,没有任何一个语词能够指称。我的心清空了所有的欲望,缩紧为最后或最初的跳动。横亘于这段历史的牙痛在我们的口腔引发深沉的痛楚。因此我尖声高唱一首切分而刺耳的曲子——那是我自己的痛苦,我承载着世界,而幸福阙如。幸福?我从未见过比这更愚蠢的词汇,这不过是徒徙于山间的北部人的编造。
就像我将要讲的那样,这个故事源自一种渐进发展的观点——两年半前,我逐渐发现了原因。这是一种迫在眉睫的观点。关于什么的?谁知道呢,也许以后我会知道。就像我书写的同时也被阅读。我没有开始,只是因为结尾要证明开头的好——就像死亡仿佛诉说着生命——因为我需要记录下先前的事实。(摘自《星辰时刻》)
哈罗德·布罗姆曾经将巴西女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评价为“把写作内化为一种终极命运”的作家,的确,很少有人像她那样呈现出生活与书写的高度契合。随着19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批评家重写文学史的诉求,作为第三世界女性文学的代表,克拉丽丝获得了欧美学界与翻译界的颇多关注。一位作家的经典化有复杂的过程,通常是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倘若一定要剥离其中所有的“附加”价值,仅以审美来关照,她也无愧于巴西、拉美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女作家的称号。克拉丽丝的魅力源自于她的无法归属,作为巴西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游牧之人”,很难把她安置于任何团体或文学流派之中。她的一生是各种方向的“出埃及记”。她原籍乌克兰,犹太教是她的文化之根,襁褓时便离开了故土,祖国对于她是异国。虽然她在各种场合强调自己是个巴西人,但在她生前,因为她怪异的外国姓氏与生理缺陷造成的特殊发音方式,也因为她随夫驻外去国16年的自我流放,世人对她的观感多停留在“异旅人”的印象上。创作上她逃避一切文学成规,拒绝传统叙事,不以情节取胜,没有开端、高潮与结局,不关心再现,只书写存在。她独立于当时统治巴西文坛的“地域主义”,在浪漫/象征主义与现实/自然主义两大文学传统的缝隙之间开疆拓土,她在写作中全然不状写巴西的风景,然而她的全部写作就是巴西。即便她把葡萄牙语视为母语,那高度诗化与譬喻化的书写语言始终属于“少数人的语言”,很少有人像她那样写。因此,对于这位拒绝一切标签与定位并在边缘之中开花结果的作家,倘若必须“强加”给她某种清晰可辨的特征,那应该是“逃逸性”。她在生命与写作的双重意义上成就了“逃逸”这种艺术。
然而,1977年,文学生命与真实生命终结之际,凭借《星辰时刻》的发表,这位巴西文学伟大的“逃逸者”完成了一场回归。《星辰时刻》讲述了一个名叫玛卡贝娅(Macabea)的北部女子一生的命运。玛卡贝娅是阿拉古阿(Alagoa)人,两岁时父母双亡,虔信宗教的姑母在暴力与压制中把她抚养成人。后来,玛卡贝娅从穷困的北部移居大城市里约热内卢,一个“一切都与她作对的城市”。她找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薪水微薄,却深感骄傲,虽然因为力不从心,经常遭遇解雇的威胁。她没有任何爱情经验,直到遇到奥林匹克(Olímpico)。奥林匹克同样来自北部,他野心勃勃,渴望社会地位的上升。他告诉玛卡贝娅,他想成为议员。而她的梦想是成为“电影明星”,这也是小说标题《星辰时刻》的源起。奥林匹克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个人条件乏善可陈的玛卡贝娅,转而追求她的同事格洛丽亚,因为她是真正的里约人,可以帮助他实现命运的翻转。
这本问寻“身份”的小说里,对镜自照是建构身份的一种途径。玛卡贝娅在镜中看到了作者罗德里格S.M的形象。这个神奇的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出现,正式进入小说,成为书中人物,塑造人物形象,言说他们的孤独。她与男友分手后揽镜自照,用口红涂满了嘴唇,仿佛找到了她所希望的身份:成为玛丽莲·梦露,一颗璀璨的超级巨星。
在格洛丽亚的劝告下,她寄望于塔罗牌的神力。经由塔罗牌师卡洛特夫人之口,她意识到自己生命的卑微。塔罗牌师的话让她第一次有勇气企盼未来:出门之后,她的生活会彻底改变。她会嫁给一个外国人,金发,“眼睛或蓝,或绿,或黑。”。玛卡贝娅满怀希望地走出塔罗牌师的家门,讽刺而又悲戚的一幕出现了:她被一位金发男子驾驶的豪华奔驰车撞倒。濒死的那一刻,幻觉的“星辰时刻”终于出现了,所有的卑微升华成了璀璨。
在这场关于个人生命的真实悲剧里,克拉丽丝的回归从三个层面上展开。首先,这是对童年与记忆的回归。克拉丽丝出生在逃离的路上,乌克兰的那个小小的村庄不是她记忆中的故乡。最早的落脚点阿拉古阿(Alagoa)才是她记忆的原点。生命的烛火将熄之前,克拉丽丝的目光深情地回望广阔的北部,一如玛卡贝娅一般干旱、空洞、贫瘠的腹地,那也是在库尼亚与吉马良斯·罗萨书写中不朽的巴西腹地。玛卡贝娅的经历中有大量的作家的童年投射:无父无母的孤儿,童年时并不丰裕的生活,压制性文化下长大的背景,从偏僻小城移居里约的辛酸经历,等等。不同于克拉丽丝擅长描写的城市中产阶级女性,玛卡贝娅矮小、丑陋、贫穷,不讲卫生,营养不良,卑微到甚至无法觉察到自己的卑微。“那个女孩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就像一条狗不知道自己是狗。她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身体里的一种缺失。如果她是那种会表达的生灵,她会这样说:世界在我的外面,我在我的外面。她仿佛是那种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的女孩,脸上的表情似乎在祈求原谅,因为她占用了空间(……)路上没有人看她,她就像冷掉的咖啡”。穷苦、卑微、善良,这些“腹地人的遗产”我们也在克拉丽丝的生命里体验。对于作品中的自传成分,克拉丽丝一直闪烁其词,不肯正面回答,直到晚年的一次采访,她引用福楼拜的名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坐实了评论家的判断。而且,如果我们相信哈罗德·布鲁姆“没有文学,只有自传”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篇小说看成克拉丽丝对人生初始片段的反观,是结束时对起点的凝望。
其次,克拉丽丝折回了她的犹太之根,在犹太文化中寻找力量与源泉。在这部作品中,宗教主要以回音的方式迂回出现。关注这一层面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克拉丽丝对主要人物性格的赋予。玛卡贝娅,这个“没有人叫的名字”,源出圣经,旧约中英勇起义的马加比七兄弟(Macabeu),是勇敢者与反抗者的同义词。表面看来,毫无自我意识的玛卡贝娅既不勇敢,也不知反抗,与那七兄弟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这仿佛是克拉丽丝的反讽,但实际上,通过这个名字,玛卡贝娅悲剧一般的死亡接近了七兄弟的英勇殉难。最后一个兄弟就义之前,马加比人的母亲说:“不要怕这个屠夫,却要证明你配得作你六个哥哥的弟弟。你要勇敢面对死亡,以致我将来能靠着上帝的恩慈,重新得回你和你的兄弟”。这样的一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抗争。玛卡贝娅是受人轻贱的,奥林匹克十分不满意他与玛卡贝娅的爱情,因为他觉得她没有高贵种族的力量。她的死亡是一种殉道,最终证明了她真的属于那个“顽固反抗”的种族,从而完成了从卑微到高贵的上升。
最后,它回归成一种对现实主义文学遗产的继承。克拉丽丝初涉文坛之时,评论界认为她是伍尔夫或乔伊斯式的作家,但她始终否认这些作家的影响。她自陈的文学先师是黑塞、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马萨多·德·阿西斯。《星辰时刻》是克拉丽丝唯一的具有社会承诺性质的作品,其主题与风格与其他作品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借用书中人物与叙述者罗德里格的话说,“我背叛了既往的习惯,实验一个有开始,高潮与‘伟大结局’的故事”。这部作品之所以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一部,多少也与此相关。1970年代跨国资本逐渐进入巴西,玛卡贝娅与奥林匹克都来自最为贫困的北部,移民到大城市里约,承受着极大的社会不公,成为了残酷的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见证人和牺牲品。在她之前写的专栏文章中,针对严重的社会不公与压榨,克拉丽丝有过克制的揭露与控诉,而在《星辰时刻》中,卑微的玛卡贝娅被车撞死的一幕把控诉推向了顶点:“玛卡贝娅倒地时仍有时间张望,汽车那时还未逃走,卡罗特夫人的话应验了,因为那车一等一的豪华。她的倒下什么都不是,她想,不过是被推了一下。她的头撞向路的拐角,倒在地上,脸慢慢地转向排水沟。头上涌出一股鲜血,出人意料的红与丰富。这说明无论如何她都属于那个固执反抗的矮人的种族,有一天,也许她会呼喊出对权利的诉求。”作为最底层的人物,玛卡贝娅从不曾表达,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但她的死亡与汩汩而出的鲜血凝化了所有的诉求与呼喊。就像克拉丽丝偏爱的“寂静”意象,无欲无言的反抗比声嘶力竭的呼喊更有力。作为创造者,克拉丽丝对于人物命运的走向是无力控制的,玛卡贝娅必然走向死亡,然而她以同情心与爱安排了一个在幻觉一般的陶醉中死亡的“伟大结局”:“她牵挂未来吗?我听着语词与语词的音乐,是的,就是这样。就在此刻,玛卡贝娅感到胃部剧烈的恶心,她几乎想吐,她想吐出的不属于身体,她想吐出辉煌的物事。一千个角的星星。”
然而,《星辰时刻》在某些意义上的回归无法掩盖克拉丽丝一贯的反叛,甚至在这部小说中,形式上的叛逆有着更深刻的呈现。对于写作的思考贯穿了克拉丽丝的全部文学生命,这使得她大部分作品都具有“元小说”性质。《星辰时刻》中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叙事:玛卡贝娅的悲惨遭遇与罗德里格的写作之痛。通过叙述者罗德里格的介入,克拉丽丝把写作的悖论与写作者的困境袒露于读者眼前。罗德里格的身份是作者、创造者,然而造物者是无力的,罗德里格在小说中最大功能是与读者交流自己的叙事,用尽全部方法否定与嘲笑自己的写作。作为创造者,他甚至无法创造出一个开始,因此在小说的开头(如果真的有开头),我们阅读到罗德里格这样的自陈:“世界上的一切都以‘是的’开始。一个分子向另一个分子说了一声‘是的’,生命就此诞生。但是前史之前存在着前史的前史,有一声‘从未’,有一声‘是的’。永远有这些。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宇宙永远不曾开始。”此处的“永远不曾有开始”的判断与后文里“背叛了既有的习惯,实验一个有开始,高潮与‘伟大结局’的故事”之间现出一种对抗性的张力,因此有必要思索一下这句话的真实性。这是一种事实?还是克拉丽丝的故弄玄虚?这到底是一种反叛,还是既有习惯的深化?对于创造者自己来说,这也是无法回答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从头到尾都在困境中挣扎的作家。他并不知道该书写什么:“关于什么的?谁知道呢,也许以后我会知道。就像我写的同时也被读。”他也不知道该如何书写:“我没有开始,只是因为结尾要证明开头的好——就像死亡仿佛诉说着生命——因为我需要记录下先前的事实。”因此,在这里,藉由罗德里格对开始的困惑,我们意外地获得了一个确定的时间点:结束,或与结束同质的死亡。
《星辰时刻》发表的1977年是一个确定的时间点,它意味着一种终结,就像我们知道这一年是克拉丽丝生命的终结一样。然而,开始总是神秘的。正如我们不确定何时是世界的起源, 直至今日,依然无法确定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真实出生年份:由于移民管理的混乱,她呈交的身份资料上出现了三个出生时间:1920、1924与1925,她终身不吐露自己的真正生辰,传记作者对此也莫衷一是。这仿佛是一种隐喻:相比既定的死亡,所有事物的出生充满了种种不定与神秘。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人类的生命初始于受孕的一刻还是呱呱坠地之时?前史的前史究竟是不是还有前史?一如克拉丽丝生辰的神秘,对于出生,我们始终无法确定起点,也许在出生之前便已出生。这是克拉丽丝真实的生命轨迹,亦是她对写作的理解与内化。写作之于克拉丽丝,是一种流动的生命形态。当我们把她的书写与她的生命画上等号,遽然发现写作/创造的起源是世界上最模糊不清的神秘。把写作比为“画蛋”并不是一个新奇的比喻,那么,人类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画下了这枚蛋?《蛋与鸡》是克拉丽丝一篇极具神秘主义性质的文章,很多评论家把这篇文章看成对书写的隐喻。在这篇被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苏定位为“Egg-Text”的文中,克拉丽丝这样说:“蛋是马其顿人的创造。它在那里被计算,是最为艰苦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在马其顿的海滩上,一个男人手拿树枝画出了它。然后用赤裸的足抹去。”为了凸显蛋及其喻体书写的神秘,克拉丽丝将对于她来说至为神秘的三样事物奉献给蛋:“我把开始奉献给你,我将初次奉献给你。我把中国人民奉献给你。”关于蛋的形成,亦即书写的过程,她无法清晰地形塑,仅以模棱两可的语言描述:“蛋可能是三角形,在空间里滚呀滚,就变成了蛋形。”她似乎想用这样的话语映射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为了让蛋穿越时光,鸡才存在。母亲就是干这个的。”她也仿佛在用这样的话语呼应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当我死去时,人们从我身上小心地拿出蛋。它还活着。”
这一连串宛如谵语般的“扯蛋”是克拉丽丝对书写的体认:书写是神秘的,也是困难的,不啻为一种生命的冒险。同时,这也是一种反讽,是对现代叙述复杂性的质疑与作者地位和能力的自嘲。“蛋依然是马其顿首创的蛋,而母鸡永远是更为现代的悲剧。”《星辰时刻》无疑是那只结构完美的洁白耀眼的蛋,通过叙述者即人物的罗德里格对自我写作的剖析,这一幕关于作者本身的更为现代的悲剧这样展现在读者眼前:
罗德里格说他写作不是因为这个事件或者这个女孩的缘故,而是因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作者是那些“在黑暗中寻找语词”的人。叙述者是全知全能的,因为他创造了一种命运。他是全知全能的,因为他仿佛知道人物所有的一切,但这种能力又是有限的,因为全部的真相只能随着书写逐步被展现出来:“我试图讲述的一切看上去很简单,谁都能做,但书写很难,因为我必须让那几乎抹去的我已经看不太清的一切变得清晰可见”。他有些犹豫,因为他自己也不确定故事的走向。由于他对他设计的主角的命运感到负疚,所以在每一页书写中都会推迟她的死亡:“我将竭尽所能不让她死。但我真心想让她沉睡,我自己也想上床说句。她可能并不需要死亡,谁知道呢?有时,人需要小小的死亡,而且至少自己不自知。” 他无法说出具体的创作过程,他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在书写:“这个故事的写作将是很艰难的。尽管这一切与那个女孩子无关,但我却不得不通过她,在我的骇然中,自我书写下一切。事实本身拥有声响,然而在事实与事实之间亦有私语”。罗德里格在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建立比较,消遣并消解作者的伟大:“她纯洁且无害,谁都不需要她。另外,我现在发现——谁也都不需要我,就算我写出了这些,别的作家一样会写。另一个作家,是的,但一定得是个男人,因为女作家会泪眼滂沱。”
这段话语固然是对作家身份的讽刺,但凭借它,克拉丽丝坚定地把自己隐藏在罗德里格身后,她又一次实现了逃逸。对于罗德里格,“只要我有疑问而又没有答案,我都会继续写作”,他的写作是为了脱离一种不可理解的困境,虽然这意味着进入更大的写作困境。然而,“逃逸”能否拯救生灵?《一只母鸡》是克拉丽丝另一篇著名的“鸡/蛋”文,文中,为了避免被杀的命运,母鸡用尽一切方式逃逸,但终于被捉,无法豁免被端上餐桌的命运。然而她在匆忙之中下了蛋,一只洁白的完美的蛋。这蛋成了她的拯救。克拉丽丝用一生的逃逸接近了这只母鸡。创造是一种拯救。创造拯救了创造者本身。这种创造是完全无意识的:“如果她(母鸡)知道体内有蛋,会自我拯救吗?如果她知道体内有蛋,会失去母鸡的状态。”而且,要求创造者完全的松弛状态,因为“如果不是这般漫不经心,而是全神贯注于体内创造的伟大的生命,她们会把蛋压碎”。之后,创造者(作者)便可以死去,不会对创造本身发生影响,就像《一只母鸡》中的母鸡,生下了蛋,与那家人过了很久:“直到有一天,他们杀了她,吃了他,很多年过去了。”就像《蛋与鸡》中的“我”,是“蛋”的携带者:“当我死去时,人们从我身上小心地拿出蛋。它还活着。”就像《星辰时刻》的罗德里格,玛卡贝娅的死亡导致了他的死亡:“玛卡贝娅杀了我。终于,她摆脱了自己,也摆脱了我们。你们别害怕,死亡不过一瞬间的事,很快就过去了,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刚刚随那女孩死去。原谅我的死亡。我无法避免,人要接受一切,因为之前已经吻过墙壁。”
随着书中人物玛卡贝娅与罗德里格的死亡,故事结束了。但死亡是小说的结局吗?死后的他试图用一个疑问句再次消解这个观念:“结局对你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吗?”
罗德里格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为了寻找答案,我们要认真阅读小说的最后几行,通常意义上的结尾:
“那么现在——现在我只剩点根烟回家可做了。上帝啊!只有此时我才想起人会死。但 ——但我也会死吗?
别忘了现在是草莓季。
是的。”
世界开始于一声“是的”,最终以“是的”结束。这一只因为种种矛盾而呈现出尖锐三角的书写之蛋,终于在不可言说中滚成了完美的蛋形。然而,凭借这一声“是的”,真的可以确定结束吗?这一声“是的”到底是历史(故事)的开始,还是前史的结束?依然是一个如蛋一般神秘的事件。罗德里格预设的那个伟大结局到底是什么?我们真的可以用1977年来界定克拉丽丝生命的终结吗?
一次采访中,克拉丽丝留下了这样的话语:“好的,现在我死了……但,让我们拭目以待,看我是不是会重生。此刻我已死去。我正在坟墓中说话。”
所以,那一声“是的”是躺在坟墓中的罗德里格所说的吧。或者,那是重生的罗德里格所说,为了下一个故事的开始。
克拉丽丝去世后一年,遗作《吹息之间的生命》由朋友整理出版,她从坟墓中与读者对话。她作品的每一次再版,每一次阅读,每一次阐释,都是她的重生。
伟大的结局就是没有结局,是把每一个结局都变成开始,是蛋与鸡相生的循环往复。
Clarice Lispector, A hora da Estrela. Relógio D’Água Editores, Janeiro de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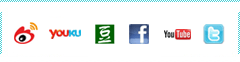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