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废墟上重建世界
艾洛
阿兰·罗伯-格里耶以写作著称于世,为午夜出版社所做的组织工作也为人称道,但同时他是一个积极的读者,其文学创作直接受其阅读的影响。他参与午夜出版社的组稿和审稿工作,创办了著名的“美第齐文学奖”,接触了大量同时代作者的创作。1980年代他在美国教授文学时,绝非仅仅在讲述自己的创作经验和谈论“新小说”干将,也在传授自己的阅读经验。2003年,他为法国文化电台录制了25次文学讲座,这一系列讲座由法国文化电台和Seuil出版社合作整理成书,我们也由此得以切入罗伯-格里耶自身阅读和写作中的一些肯綮,如他和之前以及同时代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他和批评界的关系、他和电影的关系等等。但整个讲座的中心,还是文学本身。
虽然罗伯-格里耶在讲座中谦逊地说自己在美国所讲授的只是也只能是自己个人的经验,但《作家一生的序言》这个标题表明了他的目的和野心:他不仅仅是要展示他自己作为作者的一生,也是要向读者甚至作者们讲述如何作为一个作家度过一生。
在罗伯-格里耶看来,一个作家当然要写作才成其为作家,但阅读同样必不可少,甚至是在先的。因此,罗伯-格里耶对于他认识的不少作家,甚至包括一些优秀的作家,都声称自己从不阅读,时常感到震惊和不解。据说这是为了避免受到他人的影响,为了保持和保护自己创作中属于自己的特有东西。但在罗伯-格里耶看来,“我害怕阅读会损害我的个人灵感”这样的说法是荒唐的,“为了保持我是我”而避免阅读任何其他作者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罗伯-格里耶的判断源自他对阅读与写作的基础的体认:我们生而为人,就无往不在既定的现实之中,我们的写作,无论它或者作者有多么“孤独”,都总是身在“处境之中”(en situation)。既然我们和文学的出生时间以及出生地都是既定的,既然文学总在某种既定的精神和文化氛围之中,那么,意识到我们的处境并非坏事。他引用了萨特来说明这一点,但他毕竟不是萨特,萨特由我们的海德格尔式的“被抛”处境引申出我们应该“介入”世界,而罗伯-格里耶虽然承认我们的“被抛”处境,却并不那么强调“介入”。那么,通过阅读认识到我们的处境对写作有何意义呢?面对那些自信满满但又有些畏怯的作者,这位“新小说”的干将不无幽默地说,这样一来起码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的写作究竟是在逆文学潮流而动,还是仅仅是时下最时髦的畅销书写法。先锋还是畅销,这样的差异可能并不会直接决定文学品质,但对此有所自觉对写作者不无裨益。
罗伯-格里耶不愿意使用“先锋”这个词,因为这个从军事术语借用来的词带有太强的暗示性,仿佛先锋文学打着头阵,后面就会有大部队跟上。不,罗伯-格里耶否认自己和“新小说”诸将的“先锋性”,文学是一项单打独斗的事业,每个作者的作家生涯都是一场困境,就此而言他同意布朗肖的说法,每个作者都在逐步走向他自己的沉默,卡夫卡如此,乔伊斯如此。因而我们可以说,作者毕竟是孤独的,每个作者都是一个孤独的文学探险者。想拥有跟上自己的大部队或者想做跟上先锋的大部队,这样的想法也许会在其它领域成功,但在文学的领域基本上只会带来可悲的平庸。
那么,文学应该如何创作如何阅读?罗伯-格里耶从两种文学的分野开始他的讲授。他把一种文学叫作巴尔扎克式的文学,这是前现代的文学,其中充斥着确定性,因为讲述者是全知的上帝,他知道其中的世界和众生,我们在阅读时也可以暂时离开我们的处境,进入到这个确定的世界之中,从而获得一种安定。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恶心》的主人公感到恶心的时候,并不去药房买药,反倒去图书馆借了一本《欧也妮·葛朗台》坐下阅读,因为这可以给他在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确定性和安定感,可一旦他停止阅读,他就又重陷自身的处境之中,再次感到恶心。
另一种文学是现代的文学,这是萨特的《恶心》,是加缪的《局外人》。“异邦人”并非因为他的身份而是一个“外国人”,他所不理解也不能融入的是整个世界,他离异于这个世界。这种文学的叙述者不是全知的上帝,他是一个困惑的无知者,他是一个现代人。
这一区分在罗伯-格里耶看来是他自己的写作和他所身处的“现代”的文学的基点,找不到确定性的我们只能通过文学写作创造一个世界,他借用了萨特介绍的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来说明这一点。在意向性行为中,从我的写作和我的意识投向这个世界的投射,一方面使我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使这个世界显现出来。现代的写作并不会像巴尔扎克式的写作那样让作者和读者“进入”已经准备好的确定世界,它可以也只能让作者去建构和创造出一个世界,而读者并不能随随便便进入这个世界。所以罗伯-格里耶一开课就对他的美国学生说,文学没有黑格尔式的真理,文学是一种劳作,不仅创作者需要努力去建构一个世界,读者也需要相当的耐心和劳作,因为他的阅读是在参与创造,只把阅读当做消遣的爱好者式的阅读,无法真正进入现代文学。当然,这些美国学生并不是很理解,也常常不满意,罗伯-格里耶幽默地解释说这是因为美国的学费很贵,学生们付了一大笔钱,结果却被告知,你们学习的东西其中没有真理,他们难免会感到上当受骗了,因为这样一来,岂非谁都可以对文学胡说八道,任意妄言?
我们的作者当然不会认为文学不涉及固定的真理就意味着文学可以任意为之,研究植物学出身的他很清楚科学的真理性要求是怎么一回事,但关键在于,文学另有任务(engagement)和目的,它自有自身的要求,我们要介入(engager)它,就必须懂得它的性质和处境。
罗伯-格里耶用生命和世界的流动性来批评黑格尔式的固定真理,我在动,世界在动,身处我和世界之间的文学也必须是运动的,不能是僵化的固定。他把矛盾看作现代小说,尤其是他自己以及“新小说”的作品的结构本身,并借用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中对“结构”的定义(“结构通过一种欠缺定义自身”)阐明了“欠缺”(manque)和“过度”(excès)在文本结构中的作用。矛盾使得文本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不断运动的整体,平衡不断被打破,然后再度获得平衡。这个观念来自黑格尔:罗伯-格里耶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深受雷蒙·格诺整理的科耶夫的“黑格尔讲座”的影响。黑格尔把矛盾看作生命和历史发展的动力,罗伯-格里耶反对黑格尔的真理,但他继承了黑格尔对矛盾的赞同。
罗伯-格里耶喜欢用音乐来譬喻,按照他的思路,我们可以把传统小说比作巴赫的平均律作品,一切都获得了良好的安置,仿佛一个和谐的整体,整部作品自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但即便是巴赫,在他的后期也越来越难以获得这种平衡,因为通过有限音乐材料的组合达到的平衡,其可能性也是有限的。贝多芬的音乐已经比巴赫的音乐多了许多断裂,而贝多芬后期的音乐中更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断裂和失衡。诚然,失衡之后的再度平衡可以给人另一种愉悦,但失衡越来越频繁、持久,平衡便越来越脆弱,这在瓦格纳那里更加明显,到了勋伯格,甚至整个系统都被颠覆了。
罗伯-格里耶自诩为文学上的颠覆者和“冒险者”,他把福楼拜叫作“同志”和开端者,把狄德罗看作预兆和先驱。他在讲座中大量引用了福楼拜,福楼拜描写小夏尔·包法利引人发笑的帽子花了一大段文字,可之后写到夏尔娶的丑寡妇死去的场景,却只用了几句话。按理说,前者是琐碎不足道的小事情,后者才是情节发展的大事,但福楼拜偏偏打破了这个“理”,文本的过度与欠缺是一种双重的失衡,但两者恰恰构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平衡的新平衡,这是更具活力的新结构。
但这种过度与欠缺并不能被福楼拜的同时代人所接受,他们认为,这是跑题的偏离。古斯塔夫喜欢偏离主线,舞会之后归途上的爱玛端详起了丝绸烟盒上的刺绣,这引发了一段想象。在罗伯-格里耶看来,“刺绣”是写作的一个绝佳隐喻,就此而言,福楼拜的著名宣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也具有了一种新的解读可能:福楼拜这是在把写作比作刺绣。因此,文本中的欠缺和空洞就是底布上的漏针,如果说在福楼拜那里这还是未明言的实践,到了罗伯-格里耶这里,就变成了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自觉的文学行动。
罗伯-格里耶这位布列塔尼出生长大的作家对欠缺和漏针的爱好,也源自他对法国精神的双重性特别的自觉。他强调他家乡布列塔尼的精灵鬼怪传说的传统所代表的凯尔特高卢特性,反对过于强势的罗马理性特征。他认为法语就是法国精神本身,建基于拉丁语之上的法语在他看来是一种退化了的西塞罗式拉丁语,充斥着过度的理性主义,所以他要反对狄德罗和福楼拜已经开始打破的“理”。他不仅在文学上寻找“同志”,也试图从哲学上找到突破的可能。众所周知,笛卡尔是法国理性主义的代表,但罗伯-格里耶偏偏在他最著名的《形而上学的沉思》中找到了一线缝隙,他引用了“第三沉思”中的一段话:“如果我以足够的力量梦到一个东西,我无法在醒来时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在这里,文本甚至会反对作者自身的意图和精神。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布列东身上,谈到这位诗人的时候,罗伯-格里耶反复说布列东是自己敬佩并喜爱的诗人,他和雷乃甚至想要把《去年在马里安巴》的电影敬献给布列东,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向超现实主义的致敬之作。但布列东并不领情,反倒很讨厌那部电影,于是致敬只能无奈取消了。说到这份认识上的差异,罗伯-格里耶认为自己不像布列东那么钟爱制定规则和理论,因为那会限制作者的自由和文本的可能,但布列东的诗作本身在他看来反倒是充满了神秘,并不受布列东自己颁布理论的限制,对此,罗伯-格里耶幽默地总结:应该感谢上帝!
然而罗伯-格里耶并非是反理性的,他要反对的是扼杀对立面的绝对理性或者绝对非理性,对立面之间的矛盾恰恰构成了世界和文本发展的动力。他对成双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理性/非理性,秩序/无序,主观性/客观性等等,这些成双出现的两极是理解他作品的钥匙。“新小说”常常被说成是“客观/客体的文学”,其作者是隐身的,其中的主人公并无重要性,主体退隐了,可在“新小说”教皇看来,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有评论赞美他的小说像是一个几何学家写的,他也只能略带嘲讽地说,就算是几何学家写的,那也是个非欧几何学家。这种认为“新小说”是客观文学的误解也许源自罗兰·巴特为罗伯-格里耶写的一篇评论,在《转向客体的文学》这个标题里,“转向客体的”一词是法语的objective,罗伯-格里耶认为巴特并没有在通常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所以不是“客观的”或者“客体的”,而是像照相机或者显微镜的镜头对准物体一般。这个写作/观测行为其实是主体的主观行为,但这是一个胡塞尔式的“意向性”行为,客体和主体一同显现出来,或者说,意向性的两极,我和客体所处身的世界同时显现出来。
这种对成双的酷爱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罗伯-格里耶自己追认的前辈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博尔赫斯和纳博科夫。纳博科夫与他有私交,他认为纳博科夫的所有小说作品中都有“成双”这个因素,包括著名的《洛丽塔》。纳博科夫本人也认同了他这种说法,并且告诉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传性的。罗伯-格里耶本人的创作中也不乏这一因素,这也与他的生平有关。在“成双的趣味”这一次讲座中,他仔细描述了自己的故事:从童年到少年这段时间,他时常看见另一个自己,自己的复制品、幻象,精神医生告诉他母亲,这是神经紧张的孩子常常会有的问题,就像小阿兰的梦游症和反向书写一样,这仿佛是黑格尔式的“反转的/颠倒的世界”。到了成年期,果然这些症状都消失了。但对“成双”以及复件的兴趣保留了下来,而且在某些特别疲惫的时刻,还会旧症复发。罗伯-格里耶承认,《复始》中很多场景都是自传性的,比如沙滩上的小男孩看到自己的复件出现在眼前,以及这部伪侦探小说开头的描写:主角在火车上第一次遇见自己的复件,那个男子放低了摊开的报纸,露出了与“我”一样的脸。这个场景罗伯-格里耶在韩国亲身经历过。
反转的书写或者反转的形象必须通过镜子才能看清楚,镜像才是清晰可读的:我是我的观察者。罗伯-格里耶向纳博科夫和博尔赫斯求证,是否他们也看到过自己的幻象,纳博科夫告诉他,当然看到过,但主要是在牛津期间,而博尔赫斯在他失明之前,也看到过自己的幻象。形似的复制品或者复件(Doppelgänger)也是德国浪漫派的一个重要主题,或者说,这对所有作家和所有人的想象来说,都是个重要主题。
成双和复件这个重要主题直接联系着现代文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重写。《尤利西斯》是对《奥德赛》的重写,这通过标题就已经展示给了我们,因为《奥德赛》本来就是《奥德修斯记》的意思,阿特伍德的《珀涅罗珀记》更为明显,她要以珀涅罗珀为主角重新展开故事。罗伯-格里耶的重写则极为隐秘,如果不是作者自供,读者和批评家很难发现。《橡皮》是重写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可是小说发表数年都没有人发现这一点,后来还是作者自己向一个美国来的研究者透露了内情。现在,熟悉《俄狄浦斯王》已经成为西方读者阅读《橡皮》前必要的准备。而罗伯-格里耶虽然声称2001年出版的《复始》是对他之前全部小说作品的重建,但从内容上来说,这部小说是对《橡皮》的重写。
重写不是重复,而是重建和重做,旧有的作品也许很完美,可一旦完成,它就像是流过的河水和结束的戏剧,必须重新再来。罗伯-格里耶认为文学有一些不断出现的母题,所以新文学并不比旧文学更好,不存在黑格尔式的“进步”。但他接受黑格尔的“扬弃”,复始的东西并非更好,它们具有生命的特征,会不断自我更新。英文中小说叫作novel,在我们的作者看来,这是文学和小说自我更新的要求,主题也许没有变化,但形式变化了。每一个时代都要求新的形式,每个时代都会有回应其理念和形式的“新小说”。我们可以理解罗伯-格里耶的这种想法,既然他把文学看作音乐一样“用有限材料进行创作”的活动,形式的变化就具有莫大的重要性,这种想法还体现在雷蒙·格诺的《一百万亿首商籁》之中,就此而言,他们都是马拉美的精神后裔,探索着形式和语言自身的可能。
或者,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更早的自觉的先驱——福楼拜。福楼拜认为主题是什么毫不重要,这也可以说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野。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罗伯-格里耶总在抨击他的同行米歇尔·维勒贝克,维勒贝克小说的主题总是很让人不安,比如《站台》讲的是买春之旅,但他小说的形式很稳定,没有什么让人惊异的东西,这符合现代通俗小说的特点,内容惊人甚至惊悚,但形式陈旧。福楼拜式对词句的反复打磨近乎音乐中对音色和节奏的不断调试。法院判决《包法利夫人》并不伤风败俗,只要求福楼拜把《鲁昂灯塔报》这个实名改为《鲁昂航灯塔报》。但福楼拜听到判决感到绝望极了,认为自己的整部著作都“烂在地上”了,因为一个字词的改变,也是对节奏和音乐整体的巨大变动。对一部小说来说这可能太过夸张和极端,但对于诗歌,确实往往是一字不能易,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罗伯-格里耶强调自己所受的诗歌影响,并认为散文和诗歌没有太大差别:认真的文学对形式和节奏有着在他人看来顽固的坚持。
除了文学自身的要求,现代作家和现代文学的“处境”也是现代文学迥异于前现代文学的决定性原因。这位出生于布雷斯特的作家以他自己为例子证明现代文学起始于废墟。
布雷斯特这个位于法国菲尼斯泰尔省的渔港毁于二战诺曼底登陆,为了消灭负隅顽抗的德国军队,美军把这座城市夷为了平地,用罗伯-格里耶的话来说,“没有一座建筑是立着的。”“废墟”这个观念对罗伯-格里耶来说非常重要,通过写作创造一个世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端系于此。如果世界仍然是确定的、稳定的,那我们只需进入它就可以安身立命,无需再费力去创造一个世界。但世界坍塌、崩圮了,就像是城市变成了废墟。“废墟”的坍塌状态并不仅仅是建筑或者物质上的,更是制度和精神文化层面的。罗伯-格里耶甚至在家乡毁于战火之前,在“二战”之前很久,就感到了崩圮和坍塌:法兰西共和国的政治坍塌远早于军事的败北,不,不仅仅是法兰西,整个欧洲都在坍塌,近代欧洲的精神基础在坍塌。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哲学家认为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应该为犹太人大屠杀负责,罗伯-格里耶认为这种说法可能太极端,但他也认同人本主义最终导向了奥斯维辛。
一片废墟之中的欧洲,只能从废墟出发创造新的世界。但这种重建不是原样复制之前的建筑,黑格尔说得没错,希腊是回不去了,老欧洲也回不去了,从施特拉斯堡到华沙,旧德意志坍塌了,但崩圮的还有歌德,旧的欧洲精神和昨日的世界一起一去不复返了。是的,人们还是会想要按照旧有的样子重建科隆和德累斯顿,但这些建筑和城市所属于的那个整体世界,恐怕是无法恢复了。而且,既然矛盾和大战揭示出了旧欧洲及其精神的问题,萨特宣称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无疑是要重返问题重重的人本主义。在这一点上,被萨特视作自己文学接班人的罗伯-格里耶恐怕会站在萨特批判者海德格尔一边: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必须被超越。
这也就是为什么阿兰·罗伯-格里耶会在宣布不再写小说之后多年又写了《La Reprise》这部小说。在其中他写了废墟中的柏林,由此出发建构了一个世界。这部小说已经有了中译,但译名《反复》值得商榷。通过阅读罗伯-格里耶这份讲座整理稿,我们发现,《反复》这个译名恰恰是违背作者初衷的。罗伯-格里耶想要在柏林的废墟之上,在崩圮了的威廉大街、腓特烈大街、菩提树下大街和崩圮了的歌德之上,重建他自己全部的小说作品,仿佛他自己的这些作品也在废墟的状态之中。他的这种想法源自1999年圣诞节的那场大西洋大风暴,他在诺曼底宅邸精心建构和维持了40年的园地毁于一旦,这位当过农艺师的作家亲手种植的3500棵树木全都被摧毁了。然而这场毁灭和崩圮带给他一种被拯救之感,因为一切都被摧毁了,他又可以开始重新建构了,于是他从柏林的废墟开始重新建构一个世界,也由此重新建构他自己全部的小说作品。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部作品被他命名为《复始》:在停滞和毁灭之后重新开始写作,由此重新建构一个世界。
重建,复始,这就是“La Reprise”这个书名的真意:重新开始中断了的建构。这不是重复,重复和复始是同一种运动,但方向不同。重复指向过去,复始指向未来;重复是复制过去的曾在,而复始是创造现在尚不在场的将来,一次新的出发。罗伯-格里耶指出,他引用的克尔凯郭尔明确区分了两者。克尔凯郭尔被引用的那本书的丹麦文的书名Gjentagelse(《复始》),指的是失去之后的重新获得和重新开始。[罗伯-格里耶特别指出了,之前的法译本翻译成La Répétition(《重复》)是不合适的,更晚近的译本译作La Reprise(《复始》,《重新开始》)才是正确的理解和选择。]
克尔凯郭尔以约伯为例说明了什么是“复始”。约伯本有妻儿产业和健康幸福的生活,失去了妻儿产业和健康之后,约伯并未埋怨或指责上帝,反而继续崇敬荣耀上帝,于是他又重获了新的妻儿产业和健康的幸福生活。人在生命诸阶段的阶梯上必须先失去之前的所有,才能进入新的阶段和状态:由审美的生命进入道德的生命,再由道德的生命进入宗教的生命。克尔凯郭尔说,约伯失去了多少,就获得双倍的补偿。而罗伯-格里耶开玩笑说,他不是信教者,所以肯定得不到双倍补偿,而且他之前足足有3500棵树,如果真给他双倍补偿,他的园地也塞不下。
故而,罗伯-格里耶真正希求的是通过这种丧失感和毁灭感重建一个精神和文学的世界,然后再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由这个变动的“我”,面向“无限的未来”不断周而复始地重建我和世界。人类虚构的基础大概正在于,人类总是感受得太多,理解得太少。所以罗伯-格里耶引用斯宾诺莎说,上帝全知,所以上帝无法虚构。虚构不是建造大教堂,但这以语言为材料的建构不亚于以石头为材料的建构,不亚于重建一个城市。而且,这不是对沦为废墟的城市的原样重建,而是一种艺术的重建。
今年是罗伯-格里耶诞辰90周年,比他小整整十岁的德国艺术家盖尔哈特·里希特的绘画与他的写作有异曲同工之妙。里希特按照德国战后用来修复崩圮城市的旧城市航拍图重新绘画城市的面貌,下笔粗犷蛮横,本来已经按照旧有样子完成修复的城市仿佛再一次被摧毁,然后再一次被创造,但不再是照相式的复制,而是一种外观变形的精神复现。
除了重建,文学还可以抵御。在他大加赞赏的杜拉斯的《抵御太平洋的堤坝》一书中,母亲修建堤坝抵御太平洋的潮水。研究者们知道,罗伯-格里耶也知道,实际中的堤坝其实离太平洋还有十万八千里,这一切,甚至那位母亲,都不过是杜拉斯的虚构。但杜拉斯通过她的写作建构的世界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母亲修建并维护着堤坝,以此抵御太平洋潮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侵袭,以此保护自己和孩子的家园。这堤坝类似寻找金羊毛的阿尔戈号,需要不断维持,不断修复。
文学也许不能为现实的世界做太多事情,但它至少可以为作者和读者建构一个世界或者一道堤坝,抵御太平洋或者大西洋的风暴侵蚀、损毁我们珍贵的精神园地。或者,在废墟之上重新建构一个不断展开、更新的新世界。
我们之前提到过一些理解罗伯-格里耶作品的“钥匙”(理性/非理性,秩序/无序,主观性/客观性),其实罗伯-格里耶自己反对“钥匙”这样的说法,因为有“钥匙”,就意味着有“锁”,仿佛文本是被锁闭的,等待着被打开。在他看来,埃科所说的“开放的作品”才是文本的真实状态,没有唯一的“正解”,文本向每一个读者开放着。
作为读者,我们也需要忘了钥匙和锁,同罗伯-格里耶一起,同作者们一起,重新建构一个个世界。
Alain Robbe-Grillet, Préface à une vie d’écrivain, Paris,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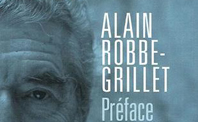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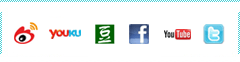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