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镜夜
隐形委员会《革命将至》
陈传兴
无论什么时期、任何地方,当危机出现时,可能是以微小征兆或是具体事件开始,此刻不可避免地一定会有夜巡者出场大声呼喊警告。他们可能是智者、先知或狂人。永远是社会的他类、他者;这些人的言语陈述,往往被一般人简化为是否符应现实状态的真或假价值判断,随后就将之逐出,或悬置在思维场域之外,不给予任何论述位置。这类呐喊陈述,疾声或静默,永远被判定为论述的幽暗魂灵,梦魇,散发令人不安的离异诡奇感。但充满悖论的是,这些幽灵总居停在真实里,甚至被当为真实,诱引出奇特的精神向度,扰动、渗透真实世界。
居·德波(Guy Debord)的《奇观社会》(1967),和隐形委员会(Comité invisible)集体匿名撰写的《革命将至》(2007),前后相隔40年,横跨两个世纪,分别见证各自时代的历史危机,作为此时此地的事件开展场所,它们各自具现实性,以及紧急立即的时间性方式─《奇观社会》盛放于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革命将至》的音乐扩散全球化,流动融合在阿拉伯春天,活在他方的革命。
如此发展形式,皆非两书原先所计划预见,某种不可言说的历史机制将它们的收受嵌入命运,逸出偶然与随意性,直接面对必然性。就像《革命将至》书中自问希腊的暴动为何会回响到法国,作者自己可能都不会预期到,《革命将至》很快会将两块绝然不同、相互隔离、甚至敌对的历史文化地理政治板块(华尔街与阿拉伯)巧妙地联结在一起。尤其特别的是,仔细审视分析《革命将至》书中内容所处理的社会事件,绝大部分都是法国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引发的暴动失序,以巴黎为其最主要的场所,如此具体的在地特殊性,从法国大都会问题出发的经验事实分析,怎么可能运作出一种普遍性效应,让不同历史文化区块的时差、历时性差异(différence diachronique)在不同的政治权力问题关系中被同时化(synchroniser)、共鸣与回响?《革命将至》运作的时间政治转化效应,已经远远超出《奇观社会》中所分析处理的西方线性(或非线性)历史时间观;比较两书的课题意向和书写方式,会让这个时间性效应差异的冲击性更强烈、暴力。《奇观社会》以定理、提纲方式,用9大章节、221条去建构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奇观社会之纯粹理性批判,严谨的历史唯物辩证构成内在逻辑,不带任何主观意见与情感涉入,摒除经验事例─除了历史发展事实,本体认识论的哲学方法处理奇观思维、意识形态问题,它意图朝向一种普世巨型论述境域。《革命将至》写在21世纪初,福柯的历史论述与哲学思维方法主导了全书的思想地貌,在其上星散分布各种大大小小的思想山脉河流,德勒兹,巴迪乌(A. Badiou),阿甘本(G. Agamben)等等。
先前主导的本体认识论,退位给在动摇分解中的本体论战役中出现的伦理学,它和形而上学终结同时踏步前进;启蒙与普世价值、永恒真理在《革命将至》书中都纷纷褪色、崩溃。福柯很严厉地指控那些想要建立普世真理的知识分子、思想家之虚幻匮乏,区域性的必要并不在于虚假的普遍共相与殊相的二元对立。特殊性、个别性、区域性,是福柯在70年代强调其历史论述、系谱考据的重要特征。《革命将至》谨守这个课题立场,一方面大量以在地现实经验描述(不是理论先行的分析)作为基础与物质内容,同时使用非常诗意感性的文学(散文)方式去书写典型的革命小册子所特有的激情、巴洛克语言风格,不畏惧个人情感感染想象的理性清晰;最后,更重要的是他们放弃哲学目的论欲望,不想建立一个抽象形式的普世理论体系;诱惑、策动与祈使的实践语用策略指向才开始的最后战斗与暴力。从《奇观社会》到《革命将至》之间的时代差距,我们看到的是思想内战,有断裂与解体,也有连续承继与扬弃,那是一个思想狂飙、浪潮急涌又退潮的年代。借用海德格尔的语言,存有片刻逼现又隐退的不断重复,所有人都急着去寻求或构建(真实或虚拟的)思想居所而不得,命定漂流和自我放逐的怀疑与虚无年代。《革命将至》出现在虚无的真实开口,一如19世纪中那些对抗黑格尔观念论所带出的黑暗虚无。不是吗?伴随《革命将至》的匆促激烈革命暴动修辞,后面是“文明的终结”,社会主义已死,“新共产主义将至”的祈使哀歌,末世论的启示录,新资本主义废墟上的未来福音书。《革命将至》写出形而上学终结,至上主权与主体性被否定弃绝的思维黄昏时代景象。《奇观社会》和解构思潮同时期,它虽已意识到主宰西方哲学思维近五个世纪的形而上学已经濒临崩塌—先后有类似像列维纳斯的形而上学暴力,质疑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本体论优先,德里达解构音声、逻各斯中心论在西方哲学史的主宰位置。动摇主体性之合理性—转捩点时期的选择,居·德波却采取回望而未断然地向前奔行;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矛盾辩证对立仍是他思想实践的主要场址与动力。对同一性、主体性的批判、颠覆与扬弃,《奇观社会》将之局限为哲学命题,语言风格问题,采用一种唯名论态度去面对、处理。
“对于支配的主流语言规则而言,唯物辩证法的推论方式,其自身风格就已是可讥和可憎、被唾弃的”—黑格尔对旧思维的破坏性,虽然释放了思维的流动性和破坏性,然而对年轻马克思来说,如此方式操作只不过是一种讽刺小品(le style épigrammatique),不能停留在诠释层面,必须反转命题主谓关系,让谓词(prédicat)取代主词,彻底改造出“暴动风格”(style insurrectionel)的语言。(论纲N°205)
此种语言命题的去主词支配位置操作,实际上只是为了掩护与强化同一性和主体性权力,依然沿用意识主体、主-客关系这些范畴去思考主体、主体性在不同场域的开展与变化,《奇观社会》书中“主体”一词,若相较于人、个体使用的数量,基本上可说是很微少。经济-社会主体,或无产者作为历史主体等等论说皆是这个同一性观念论哲学逻辑表现:历史主体是一个“自我生产的生命体(Vivant),变成其历史世界的主人与拥有者,以其运作意识方式存在”(N°74)。社会主体出现在相互支配共生的社会无意识和自主经济暗流相互斗争中(N°51, N°52)。主体、主体性在《奇观社会》中似乎从未受到彻底批判,更不用说将之颠覆,即使是直接面对的阶级斗争问题中,也至多仅只是悬置社会主体作为待思的对象。奇观魅惑主体,给予幻象欲望。奇观提供另一种实证性,另一种真实给主体,满足主体。奇观分裂人,隔离人与世界,保留并悬置意识主体在无尽影像回映。
《奇观社会》书中,人、人性、活生生的人、工人、个体高频率出现,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称之为《奇观社会人类学》。有趣的是,《革命将至》2009年增补后记中,有一句话归纳全书:
“归根究底,其实这是一部关于我们总在战争的人类学,所有一切都是人的想法所造成。”(页163)
奇异语调回响在人的终结、历史终结、文化(明)终结,所有终结的终结废墟上。战争人类学,接替延续奇观社会人类学的历史异化矛盾运动。人还存在?抑或人与存在的问题仍在衍异变化中?
《革命将至》导论立即地点出当前社会、文化绝境所处的历史断裂位置,历史事件(“2005年11月的纵火事件……和以往的暴动形态间产生了决裂”),这种处境同时揭露了当下哲学匮乏不足之处,本体存在论-政治性与社会的崩解撕裂,认识论的丧失共同经验的语言,也欠缺解析问题的思维与方法。彻底匮乏的主体残躯如何能对抗更为全面的泛视控制与安全治理的压迫,极端的脆弱无助被动,或是选择决定行动,创造新语言情境。《革命将至》的作者们在这样状况下,必然要放弃旧形而上学范畴语言与思维─《Tiqqun》第一期(1999),“何谓批判形而上学?”已尝试指出形而上学终结之转捩点变化─不论是否定风格,或暴动风格,那一类哲学书写都丧失其合理性,唯一的出口,就是剥除风格,单纯大写的“暴动”自身。基于这样的思维逻辑,不可能存在任何作者去书写“将至暴动”,他们至多只是倾听者,抄录下危机崩裂的微音与场景。此所以集体匿名,与隐形之必然。书写为了自我擦拭与消失。
历史位置决定不同的透视观看,透露书写者作为历史主体之特殊性。居·德波作为《奇观社会》作者,签名,坚守历史连续性观点,不回避长时段历史可能陷入历史主义困境矛盾,他深信《奇观社会》揭露资本主义本质秘密的普世价值,法文第三版(1992)前言中,他强调第三版对1967年第一版一字不改,原因在于“只要长时段历史的总体条件未被摧毁,这理论将会是头一个去定义其正确性。(历史)阶段的连续发展只不过是证实与表征此处反覆推演的奇观理论可被认为具有历史性,以一种较狭窄的意义去看:它见证1968年争论时期中那可能在1968年中认识的最极端位置。”(gallimard,1992,pp 7-8)
争夺历史与记忆,也即是对抗奇观机制占据与取消历史代之以戏剧化的伪-事件(N°157, N°158)。
《革命将至》坚持历史终结、断裂的非连续史观,引用科耶夫(Kojeve)在二战结束时谈法国国族历史终结的论点,必须打破法国国族历史迷思,解开时序错乱(anachronisme),才能从国家控制中释放革命的可能性(页95)。然而,《革命将至》的作者们并不想依赖历史学家的诠释去掌握历史,他们弃绝另一种历史主义:“文明是否已死,那是只有历史学家才会感兴趣的问题。历史学家要寻找的是事实。我们必须要作的是决定。事实是一种修辞技巧,决定是一种政治行动。”(页101)
作为历史基础与动力的“真理”也同样地被质疑、相对化,那只是“西方”的某一种思维范畴再现,去除生命内容的片面真实(页99)。形而上学瓦解后,一切都被相对化、虚无化。怀疑或死亡。主体、主体性不能回避地趋向自我取消的命运;我、自我、己身以何种方式去体现如是苍茫中黄昏,去扑取风中飘散的同一性与主体碎片,抑或碎解的主体残骸浮游汲取、拯救沉溺中自在裂解的自我?我、自我裂解形式是否能对应主体裂隙?《革命将至》模拟嘲讽“我思故我在”的主体形而上学霸权瓦解,重新以全球化广告语言“I am what I am”开启全书旅程,倒转“cogito ergo sum”所带领支配的自我的庞大哲学史境域权力;用通俗的英美商品经济语言,去撞击承自经院哲学的拉丁文思维范畴术语。语言策略毫无保留地撕裂主体(性)残骸残存的殓衣破片,黑暗的死亡之舞。兰波的一首诗《地狱之夜》(Nuit de l’enfer),一位自杀亡灵游走地狱独白,如同但丁神曲地狱场景,他倾听那些被罚判永世沉沦地狱受苦的自残、自杀者,自我主体的幽魂,碎裂的人影,转用笛卡尔的断言:
“如果罪该下地狱者是永恒
一位自残的人是该下地狱,不是吗?
我相信地狱,故我在
这是教义的实现
我自囚于受洗礼中。”
“我相信地狱,故我在。”我思实际上并未能阻止怀疑的入侵,我思打开我的地狱之门。我的现代性,地狱。
类似的隐喻的,《革命将至》也是自我,主体消解作为当今正在溃亡的西方新资本主义世界七圈地狱图的第一圈。我即是地狱:
“‘I am what I am’。西方世界向四面八方进攻,化身为他最疼爱的那匹特洛伊木马。在我和世界之间,个体和群体之间。束缚和自由之间制造要命的矛盾。自由并不是摆脱一切束缚的姿态,而是面对束缚、展开行动的实践能力……换句话说,如此像个地狱。把自己连根拔除的自由一直都是自由的幽灵。当我们甩开了阻挡我们的人,我们同时也失去对他施加影响力的机会。”(页23)
这匹西方征服世界的特洛伊木马,“同”(même)的哲学主权掩藏在“同一性”(identité)的意识场所下向世界扩散,整部西方哲学史就像奥德赛在特洛伊战役后,漫长困难的海上漂流返乡史诗,自我不停地尝试各种途径与策略去寻求回返自身,建立同一性的至上王国,对抗“他”(Autre),并将之放逐于外边,除权。从“认识自己”哲学命题,“自我关切”(souci de soi)之伦理实践与机制,随后的早期基督教的“自我诠释学”(herméneutique du soi)揭露自我背后隐藏的另一深层面,指出“他”之黑夜居所,经过笛卡尔的怀疑论自我开启主体形而上学主权基础,到了黑格尔手里终于统一“同”的哲学王国,“同一性”得以返乡,“在己”(être soi),“为己”(pour soi)。实现了观念论哲学的精神恒常大等式,自我等同,排他。“他”被放逐,徘徊在浪漫主义和其后裔虚无主义中,衍生出漫长的未完成哲学计划。在“同”的哲学王国领域,自由,“把自己连根拔除的自由一直都是自由的幽灵”,“把自己连根拔除”(S’ arracher),从自由自身中剥除出来的自由残影,没有实体内容,只有幻魅形式,因为在“同一性”之坚持下,自由在面对他者、非-我,它向后隐退,自我剥除成为空洞,此即是列维纳斯所说:
“‘同’的帝国主义,它就是自由的本质……如果自由将我(me)置于直接碰撞非我,在我(en moi)和在我之外(hors de moi),或假如它要将之否定,或拥有之;(总之)在他者(Autrui)之前自由退缩。”(“Totalité et Infini”)─Emmanuel Lévinas─Martinus Nijhoff, 1971,P.86)
“在己”、“为己”的自我完成之政治下,“自我”以隔离看待世界以及和他者的关系,而他者面对如是自我,有意或无意,会在意识场所引生关系,入驻或改变,抗拒自我的空洞自由幽灵。束缚和自由的矛盾悖论将会无尽开展。
《革命将至》选择“自我”的矛盾课题作为全书开头第一章,原因就在于针对“同”、“同一性”的哲学帝国支配了西方资本主义之宰制现象,从工业革命到新资本主义,总体生产机制,想象与物质,生产与交换;思维意识与实践方法技术,在在都存在“同”与“他”的矛盾对立冲突与阴影。“自我”的问题居于其中枢纽位置,《革命将至》微妙地将这些问题由第一章(现象描述,定义,解题和假设)衍生派分到全书上半部的其它六圈矛盾社会政治场景。书的第二部分经过七圈的剖析修补,指控与自责,“自我”、“同一性”被反转,里外倒置,否定性的矛盾参与救赎实践。在这内战场域中,自我脆弱被敌对他者所强化,同时等待新共体的他者之庇护救助,被抛掷到荒漠世界,自我救赎于世界破坏毁灭。《革命将至》的思想纲领,源自想象的群体机关刊物《Tiqqun》在第一期中的一篇论文《批判形而上学》里,简略描述所承继的当代思想,居德波的《奇观社会》使用形象(Figure)去穿越所有社会场域的政治经济操作,揭露出奇观逻辑的异化抽象工作:“被显露的物体和其显露模式混杂不分”(P.13),以此作为Tiqqun实践行动的战争机器。而作为一种现代革命的批判形而上学思维核心,则是以德国观念论和犹太神秘主义的Tiqqun思想概念混合方式出现(P.15)。异质混血的杂合,将“同”、“同一性”和“他”、“他者”矛盾并置,相互抗争,犹太神秘救赎教义渗透观念论的自我帝国。但不仅是思想概念的混杂,超验、先验的外方离心运动打破内存本质论的自我反复,封闭向心空间。《批判形而上学》文章里明确地指出其所依归的Tiqqun思想,是16世纪卢利亚(Issac Luria)所诠释的卡巴拉教义系统中的一个教理与实践原则。《革命将至》经过七圈毁灭败坏世界图像巡礼后,最后的救赎行动,反映了卢利亚的神学宇宙体系以及Tiqqun olam的终极重建修复世界的工作。卢利亚卡巴拉教义思想影响各种形式的社会改革行动,从社会互助救济到极端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革命。
《革命将至》尝试将Tiqqun神秘思想化为极端社会行动策略。人类、世界的救赎革命实践,悬置“神的观念”(idée de dieu),封闭先验向度的开口,又再一次矛盾折中接受形而上学,同一性本体论的隔离,《奇观社会》第20条论题充分表露了神学/哲学悖论困境,只能在实践中用折曲的掩盖与悬置去处理,而不可能直接面对解决:
“哲学,作为隔离思维(La pensée séparée)之权力,以及隔离权力(pouvoir séparé)之思维,它从来不可能藉自己去超越神学,奇观是宗教幻象的物质重建。奇观技术无法驱散宗教云雾,在彼处人将从自己被剥除的权力放置在那儿:奇观技术仅仅将它重系在一个人间基地之上。由此,最为人世的生命变成不透明与不可呼吸。它不再抛回天堂,而是将它的绝对回绝和虚假乐园收容在自身之内。奇观是人在天堂的权力(被)放逐的技术实现;在人之内的终极分裂(la scission achevée)。”(同前。P.24)
论题中使用的词语,“重建”、“除权”、“放逐”、“不透明”,直接地借用神学语汇,甚至非常接近卢利亚的Tiqqun思想语言范畴。如果宗教是重建、重赎被原罪沾染破坏的世界,奇观用幻象去重建这重赎,无限延迟救赎,修复原初创造,让灵光被封锁,那么《革命将至》的Tiqqun工作就不仅仅只是打破奇观幻象,解放其后的宗教与信仰,召唤神学必要性并不是其终极目标,从社会瓦解混乱中去重建世界,并不是遵从圣经或任何宗教规则的行为,而是绝对的实践,某种伦理救赎行动,重现失落的创造灵光,这才可能是《革命将至》从犹太神秘主义中汲取实践行动的思维原则之原意,基于此,或许它才可能回避开先前所有神秘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所陷入的救世主乌托邦困境。
《奇观社会》强调,“观看”范畴是西方哲学的致命弱点,制造“奇观”的原罪机制(N°19),而人的内在终极分裂是观看逻辑所造成的效应与结果,全书甚多论纲都用在分析整个机制运作过程。自我的分裂在《奇观社会》里被认为是奇观之结果,而不是其条件与动因;如此分析方式着重在自我与社会的拥有存在关系,忽略了自我分裂的先验条件,颠倒了奇观与自我的动能性矛盾政治。《革命将至》第一章中尝试不同途径去重新检视自我,自我裂解和“同”、“同一性”的矛盾冲突在当下社会情境世界中,回返自我的课题场域,穿越奇观,直接面对质问自我在同的帝国政权当中;经过上个世纪,从海德格尔的《存有与时间》分析存有(Dasein)所提出的有名课题:
“因为Dasein在任何状况下都是属我的(Jeimeinigkeit),当我们称呼它时,我们永远必需以人称代名词:我是,你是。”(第9节,Dasein的分析基题)(“Being and Time”─Martin Heidegger. Translated by John Macguarie & Edward Robinson. 1962. SCM Press. P.68)
我的同一性、总体性就不断被质疑,以不同的方式去裂解自我;他、他者的权力也开始受到重估;伴随的哲学领域内形而上学终结、本体论封闭与伦理学入场,《革命将至》第一章对自我的召唤与质疑基本上呼应了这整个思潮的回响与共鸣,法国上世纪80年代后的思想主流。在中文语境中,欠缺明确语汇能够充足表达我与自我的分裂的各种单子状态,以致中译本《革命将至》第一章中,甚多段落失去清晰意旨,模糊了原文的语意场域以及其后所带出的修辞张力,哲学语境也因而被阻塞。译文之不足,主因在于语言文化差异与中译哲学语汇匮乏的两种历史条件,限制译者的能力而造成展望视野不足,无法迎纳他者语言进入母语居所。
关于我、自我的法语哲学语汇,大体上涵盖几个人称代名词:“Je”(主词,第一人称),moi(主语与宾语),soi(第三人称,反身用语,经常和Se并称)。Soi,在福柯的晚年伦理学研究大作《souci de soi》造成极大回应后成为普遍思想论述场域语用现象,脱离开先前被局限在哲学范畴内的特殊语用─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观念论法译本开启moi-soi的分裂对立矛盾,海德格尔探讨存在与“我性”之问题,萨特将之扩充成为存在主义哲学标语 en soi, pour soi,列维纳斯借径现象学、海德格尔存有哲学深化moi-soi之分裂矛盾裂隙,碎裂我、自我性,他、他者于此浮现上升。福柯的历史伦理学谱系论述,重新给予soi和同一性哲学权力王国一个历史向度。我、自我的问题也随之重回哲学问题场景,利科(Paul Ricoeur)的《自我如同一位他者》(soi-même comme un autre)(1990,大陆译为《作为他者的自身》)即是对这问题的回应,他重新整理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哲学关于自我、他者的理论,兼及欧陆外英美分析哲学之处理讨论。尝试在列维纳斯哲学之外提出另一种“他者”、“他性”理论。
对于如此庞大复杂关于,我、自我概念范畴的思想史发展,《革命将至》概括地认为这无非是一个自我循环的唯名论矛盾,一个彻底失败的计划:
“这些概念历经数十年的变化,只是为了完成纯粹的同语反复(la pure tautologie。)我=我(Je = Je)。”(页20)
Je = Je(我等于我),永恒的大等式,绝对形式概念不容许任何我、自我逸出思维意识场域去获取任何内容。我、自我是否可能逃遁出这个自我循环困境而不被抽象概念化,被整合在同一性,能真正有其内容与存在?《革命将至》描述社会操作原子化去裂解个体过程,同时又将之隔离,去营造出一个自我撕裂成不对称的两个自我,精神耗弱的内在空洞我和社会化接受命令服从的表象我,两者间的矛盾协商为符应社会生产-消费过程所需求的,“不断在适应的主体”(sujet indéfiniment adaptable),也即是自我改造成“普遍弹性”(la flexibilité générale)的一种反转回溯退到婴孩期,没有思维,只为维生。自我反思的大问题,“我是谁?”(ce que je suis),不会被提出,因为自我根本不存在,或是它早已被纳入永恒等式内,认同同一性:
“我们感到不安,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矛盾且信仰一个永恒的我(permanence du moi),对于塑造我们的一切反而不太在意。”(页23)
同一性(identité),永恒的我,遮蔽或取消所有能拥有诉说能力的“存在”,这个存在是“我和世界的关系”,“独特但又共享的生命世界”,也就是对抗单子化、碎裂个体成封闭的唯名论我之操作,回到创造状态,Tiqqun文章所提示的向度,以生命、肉体给予我面貌和形式:“……每个人都是创造物,都在相似处理混杂着独特性,我们都以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共同组成这个世界的样貌。”(页25)同中存他,相似性共容特殊性,感性(sensibilié)藉由moi-soi的收缩开阖去扩展在生命肉体,逃出同一性的我之绝对概念,和世界对话。
逃出Je = Je的永恒等式概念囚禁,让“我的假设”(hypothèse du Moi)裂隙(页26)自我扩大到彻底瓦解、无底,此刻,方才能将自我问题反转成对抗我(Moi),同一性的至上权力的革命力量:
“每个人的身心问题既可以被当作事实看待,也可以将‘我’这个假设彻底瓦解……个人问题一下子变成抵抗眼前这场战争的行动依据,它变成造反的能量核心。”(页24)
《革命将至》用大写字母表达“我的假设”中的我(Moi),大写Moi占据全文的书写主位,相较于Je,soi(la quête de soi)(追求自我),toi,me;唯一出现小写moi的例外处是在作为谓词使用:Je suis moi(我是我)和否定的ne sont pas moi作为主格的大写Moi支配小写moi,此种语言情境无法在中文语境中找到对应表述,这是否曲折显示中文思维存在不同的自我范畴场域,等待开启?(吾,自,我,己,等等语词的思维范畴与前述历史场域所支持与对应的语言体系,语意生产过程,待思!)Moi和moi的不对称“我”之权力位置与意义;Moi的主权既不是先验性,也非内存,它来自于复杂的我之内化分裂矛盾运动,产生于Je-moi-soi三者间的回旋离心与向心的系缚于解脱运动所划出之世界情境之力场。在列维纳斯的哲学体系中,他、他者论述产生的原场域。它陈述moi和soi的关系,moi是先天地像复本一样退回到soi,与soi系缚在一齐,即使这样的关系是沉重、黏滞,但唯有这样moi才能成为moi,成为soi;因此Je之存在不可免地就被这个不得不有的moi-même所阻塞,然而这也是其物质性内容与自由之所在。
反过来说,那么大写的Moi之自由和其物质性也必然决定在Je和soi-même的系缚状态,而主体涌现有如俘虏一般(见“solitude et matérialité” in 《Le temps et l’autre》, Fata Morgana, 1983, pp 37-38)面对大写Moi之至上权力,moi,soi和主体的状态,就像《革命将至》书中描述当前我的特殊性秘密:
“就是把个人自我(Moi)维持在一种永远有一半毁损、另一半慢性衰竭的状态。耗弱的我、抑郁的我、自我批评的我、虚拟的我,这个我其实是不断在适应的主体……”(页22)
“不断在适应的主体”点明了句中所陈述的不同的我之现象,并非是经验个体的我,它毋宁是我的自我裂解单子化去符应外在的东西,某种类似列维纳斯所定义的“去核的中空主体”,去容存从大写Moi中逃出的小写moi。这个中空主体和不安的小写moi,并不能营造稳定的自我。就如同下一段落指出经验世界所构筑的表象聚合并“不是我”(ne sont pas moi)。真正的我,不是由同一性(identité)决定的世界关系,是交涉存在,生命存在,有语言诉说权力的我(je),非永恒的,在时间中移动的我、自我(Moi),自我的假设(I’hypothése du moi):
“人们尝试印在我们之上的形式”(页25)
大写的我(Moi),一个至上形式,支配(自我)概念的主权宰制,moi如何在其中形成?从大写Moi剥除出来的moi:
“小写moi作为小写moi,也即是从其概念中脱逃出来的moi,我称这情境为脆弱性,绝对罪恶感,或是绝对责任……moi作为moi,在这种极端个别性,这并不是一个自我反思soi的情境,它对其所施之恶负责。Moi是被迫害,在原则上,它应该对加在其上的迫害负责。”(《De Dieu qui vient à l’ldée》P.135)
小写moi作为小写moi,从Je = Je的永恒同一式循环悖论逃出。这个和soi系缚在一齐,但又欠缺对等关系的moi,在同一性的反复循环中未受到对等待遇。列维纳斯在《Autrement qu’être》给予小写moi一个明确属性定义,它是一个极端脆弱,臣服于一切的被动性实体:
“小写moi,是一个具有某些道德特质,它以具属性实体方式承载之─或是在其变化中产生的偶然,基于它在soi的被动性(passivité)或是激情中所持有的特殊独特性,也即是这个臣服从属于所有,或替代的无间断事件。这个事实,存在它非─拥有(déprendre),自我掏空其存在,将自己里外倒翻(à l’envers),这或许可以说是一个“它于存在”(autrement qu’être)事件。臣服,既不是虚无,也不是超验想象的产物。”(《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E. Lévinas. Martinus Nijhoff, 1974 (pp. 184-185))
因为moi的实体特质,自我性(ipséité)只会选择moi,而非Moi为其唯一的选民:
“自我性,是一个特权,或是一个不公正的选举。它自我选取小写moi,而非大写Moi。唯一被选择的Je。臣服从属所作的选举。”(同上,p.201)
从这两段关于moi的解析,重新检验《革命将至》,将大写的Moi套用在耗弱病态的个体上,其实暗地里让moi从大写Moi主权中逸出,并动摇Moi的概念至上性,和同一单元性:
“把个人自我(Moi)维持在一种永远有一半毁损,另一半慢性衰竭的状态……是不断在适应的主体。”
这句子描述的不仅是一种德勒兹-瓜达里的“精神分裂”式的单子自我,moi对Moi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会孕生出不同的我之政治。
脆弱,无能,病态的个人小写moi,其不适应性和脆弱被动性,让我自己内部的分裂斗争、我的内战,转化成自我流放,“我是他者”(Je est un autre)韩波诗句表征了我之他化,“他于存在”,自我性(ipséité)藉由他者之助穿越我(moi)的概念,将我(moi)从概念中剥除选出,不再让Je能回返逃避在moi概念当中(Lévinas,同上,p.227),《革命将至》第2圈,从历史与政治去看自我性建立是如何面对他,他者,以moi─soi的变化,自我撕裂,大写的Moi国家如何去改造成想象公民共同体:
“我们的历史就是殖民史、移民史、战争史、流亡史,是一切生根立足的基础皆被毁灭的历史。在这个历史里,我们变成这个世界的异乡人……法国人对外国人的恨,交杂着对自己身为异乡人的恨……移民在这个国家占有一个奇怪主权地位:如果他们不在法国,法国人恐怕也不存在了。”
移民的主权,也即是同一性、认同的不对等性,我的存在依赖着他者;对他者的责任,也即是我的自由之条件;迫害、执念妄想联系,系缚我与他者在一个共同的自我流放情境。自我性,我从来是焦虑、扰动与不安,自我贫化和大写Moi之秩序混乱,失去支配主权是一致。大写Moi只能用工作、劳动去改造moi-soi,让从属臣服停留于经验世界的封锁,用异化的都会空间衍异这个从属臣服关系,不让它逃遁反转成责任要求与指控。新环境伦理道德,延续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支配moi、soi与世界的关系,没有时间性,被掏空的soi支撑没有主体性的空心主体,像Tiqqun期刊文章《布伦理论》中的布伦,没有面貌、特质的个体,彻底被隔离,不可能开向他方、他者的我,永远沉溺在恶之平庸性中而不自知的一种极端的恶之共谋者。我的能动性被转化为原物料,可交换生产与再生产,而所获得的是被规定的,被移转的被动能动幻象,和时间残骸。革命的可能性就在自我之内爆与流放中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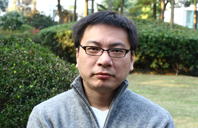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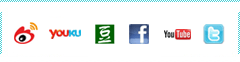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