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俞冰夏
这是一个你越来越分不清楚畅销小说和文学小说之间区别的年代,这一年,看似默默无闻一炮走红的查德·哈巴克(Chad Harbach)靠一本讲棒球的小说在文学界打了个大满贯,但你知不知道这个哈佛和弗吉尼亚大学写作班毕业的人90年代开始就已经混迹文学圈?你又知不知道《外野艺术》(The Art of Fielding),这本被屡屡与大卫·福斯特·瓦莱士相比的新时代文学大作出自于Litte,Brown这样一个出畅销小说尤其是青春畅销小说的出版社?(哈巴克与大卫·福斯特·瓦莱士的相似之处大约仅限于前者喜爱后者)。圈子的力量是伟大的,而2011年的欧美文坛离不开查德·哈巴克,或者25岁来自南斯拉夫的天才少女提亚·奥布莱特(Tea Obrect),或者史蒂芬·金更为文学的尝试,又或者晚于很多市场一年多才上市的英文版《1Q84》——这最后一条,我总觉得是个营销阴谋,如果《1Q84》不是在2011年上市,这个依赖于名誉大过任何一切的市场在这一年简直要陷入一种尴尬的真空。如果你仔细看,整个欧洲与美国已经找不出多少妇孺皆知的大牌高产小说家,可悲的是仅有的那几个——保罗·奥斯特、乔纳森·弗兰岑或者米兰·昆德拉,都直接跳过了2011。
没有大师的年代
不要问下一个小说大师是谁。这个人不存在。好几年来,终于有一个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得了诺贝尔奖,但诗歌已经有如僵尸,真正的小说离得也不太远。2011年,最受瞩目的作品是布克奖得主朱利安·巴恩斯的《一种尾声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这本书短得惊人,只有150页。在所有巴恩斯的作品里《一种尾声的感觉》完全排不上号,但它正是今年各国书店的头牌。《一种尾声的感觉》的语言当然是巴恩斯的精致,故事却实在说不上新鲜——主人公儿时的朋友自杀了,使得他不得不面对一段早已遗忘的过去。读这本小说,有时候你会发现浪漫主义电影的桥段,比如一个数学公式里镶嵌着四个朋友的名字。“有积累。有责任。但除此以外还有不安。还有很多的不安。”这样多愁善感的句子多过了巴恩斯在《福楼拜的鹦鹉》里那种具有更多层次感的机智与知识分子的敏锐。
巴恩斯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英国作家,他时而是个文化精英时而又贴近群众的泪点或者笑点——一众当红英国作家走得都是这样的路线,从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到杰夫·戴尔(Geoff Dyer),他们讲的总是小生活的故事,语言总是精致优雅又繁复罗嗦,格局之小和这个时代的文学局面可以说是相得益彰。这是个不需要大部头也没有大师的年代,写作是种工作般的行为,它不超越任何东西。每一年的布克奖名单总是招来很多关注,年复一年,这种关注越来越失去意义。你既找不到文学的新尝试,也看不到任何除了讲一个故事以外的意义。今年的布克奖,除了得奖的巴恩斯以外,进入短名单的作品题材让人摸不着头脑,老派女作家卡罗尔·波尔茨(Carol Birch)的《贾马尔奇的动物收藏》(Jamarch’s Menagerie)讲的是个男孩遭遇老虎的故事,黑人女作家艾斯·伊杜格言(Esi Edugyan)的处女座《半血缘布鲁斯》讲的当然是个黑人在二战时期的故事。英国小说总有那么点自恋的气质,好像故事要追求越小越偏越不当代越好。唯一值得关注的反而是A·D·米勒(A.D.Miller)的《雪花》(Snowdrops),这个《经济学人》驻俄罗斯记者的小说处女座把视野放到了新的俄罗斯,叙事里有种新闻写作的紧张感,而不是传统英国小说贵族式的敏感与慵懒。
再顺着文学奖寻找下一个大师是件不靠谱的事情,但欧美文坛从来是个爬名誉阶梯的地方。这是一个连已经故去的斯蒂格·拉尔森都必须被复制的年代——今年北欧悬疑作家仍然走在光明大道上,前有挪威的乔·内斯波(Jo Nesbo),后有芬兰的贾尔克·斯皮拉(Jarkko Sipila),谁能想到“斯堪地纳维亚犯罪小说”也能成为一个“类型”,更有趣的是这批北欧作家有个共同的特质,他们似乎都与斯蒂格·拉尔森一样,曾经或者仍然在做记者。可怕的当然不是类型小说的批量复制,而是类型小说对正统文学的侵入。查德·哈巴克的忽然走红是个奇怪的现象,这一切机缘巧合贴得太天衣无缝,正是美国流行的橄榄球电视剧《周五夜晚》(Friday Night Lights)要闭幕的时候,就连电视都需要下一个德克萨斯体育爱情故事。这个时候我们迎来了今年最受宠的一个名字,他受到的追捧让人难以理解,这本书里充满了棒球术语,任何一个缺乏棒球基本知识的人都无法读完前五页而不被类似“短停”(shortstop)之类的词语难倒,更不用说《外野艺术》这个名字在小说里是本棒球秘笈。
查德·哈巴克像一个写作班里很多的、热爱写作更热爱体育的普通男青年,他碰巧却有强大的人脉。这个纽约嬉皮文学杂志《N+1》的编辑不知在布鲁克林的酒吧里交了多少出版界和媒体界的朋友,使得这场炒作几乎具有历史意义。“圈内人”捧出来的畅销书作者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无关于写作的质量,而是把明明是类型小说的《外野艺术》在文学境界上彻底提高了一个档次。它成为了《纽约时报》等各大主流媒体的年度十佳小说之一。它被拿来和过去的男性主义作者(Macho Writer),比如瓦莱士或者海明威相提并论——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海明威固然是斗牛爱好者,对此费尽笔墨,但他从来没有局限于在斗牛里看斗牛。
2011年,整个欧美文坛没有一部让所有人惊艳的作品。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又一本遗作《第三帝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本来就不应该被发表。从《巴黎评论》连载的一开始,所有人就都意识到这是个失败的小说,以至于在连载的第二期上《巴黎评论》不得不在封面上印了“这部分情节更扑朔迷离”这样怪异的宣传语。杰弗瑞·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虽然个性乖张,却爬不出准一流作家的行列,《婚姻情节》(The Marriage Plot)中规中矩乏善可陈,讲得是一个大学毕业之后成长的故事。村上春树的《1Q84》固然让欧美读者有所期待,却谈不上是村上春树最好的作品。2011年值得尊敬的小说家是史蒂芬·金,《11/22/63》反而是本真正的文学作品,用一种非常聪明巧妙的方式牵连了出了一个有关刺杀肯尼迪凶手的故事。
当然,这一年也不是没有一些精彩,尼克尔森·贝克(Nicholson Baker)的《洞之屋》(House of Holes)荒诞不经,口味重而具有颠覆性。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重版的小长篇《火车梦》(Train Dreams)写的是美国大西部开发时期的火车旅程,与他以往的作品一样具有空灵的毁灭感。高产的弗朗西恩·普洛斯(Francine Prose)语言依然清脆而黑暗,《我的美国新生活》(My New American Life)里反讽和调侃玩得恰到好处。
视野望向哪片大陆
欧美文学界缺乏新鲜的刺激并不是新鲜事,一个波拉尼奥掀起如此大的浪潮并非偶然,因为在欧美,像小冯内古特或者约翰·厄普代克这样的“作家中的作家”已经越来越少,如今也只有米歇尔·维勒贝克对得起这样的名誉。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商不得不把视野越来越多得望向远处。翻译小说曾经在欧美毫无市场可言,如今像村上春树这样的外国作家早已占据了头牌位置,并且出版商正挖空心思地发掘更多的斯蒂格·拉尔森或者波拉尼奥,如今年轻作家的阵营里非英语国家出生的已经超过了半数。
实在不行,还有蒂亚·奥布莱特(Tea Obrect)这样的半外国作家。年轻的奥布莱特文字里有种小公主的气质,它细致、耐心、富有真情实感,甚至有时单纯无辜,但很奇怪,这本2011年除了《外野艺术》以外又一本被广为推崇的小说《虎妻》(The Tiger’s Wife)有的时候读起来好像一本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巴尔干文化指南。差不多的题材,曾经的《恶童三部曲》造诣要高得多,在欧美的反映却几乎从未那么热烈。当然,欧美文坛需要这些东西,问题是,应该往世界的哪里看?
亚洲文学在欧美近几年的表现非常之差是个不争的事实。几乎没有一个除了村上春树以外的亚洲作家找到任何一点的突破。这里面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翻译的困难,而是市场的不对等。拿中国来说,欧美文坛要找的是比郭小橹质量更高也更有市场潜力的又一个郭小橹,富有西方意义上的冲击力和政治性(女性主义、种族、压迫等等),而中国愿意推的却是文学性很强,题材又十分乡土,让英语读者感到隔阂生硬的50、60后作家。去年《格兰塔》杂志出了本西班牙语小说特刊,今年《格兰塔》在讨论的是自2005年以后的又一本非洲特刊。非洲是2011的关键词。另一部被广泛追捧的处女座小说是《开放城市》(Open City),来自尼日利亚出生的特于·科尔(Teju Cole),写的是曼哈顿,当然也融入了非洲的记忆。在南美、亚洲和中东各自被注视良久以后,非洲是仅剩的一块文学处女地。但真正出自非洲的那个小说新星,在库切之后后继无人,且属于非洲黑人的文学离良好的发展越来越远。
另一本非洲关注的作品是肯尼亚黑人小说家Binyavanga Wainaina的自传体小说《有一天我会写这个地方》(One Day I Will Write About This Place),这个相对年轻的作家是近年文学圈非洲声音的最大代表。他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打油诗,叫《怎样写非洲》:“永远在标题里写‘非洲’或者‘黑暗’或者‘丛林’。小标题可以包括‘赞自巴尔’、‘马萨伊’、‘祖鲁’、‘赞贝兹’、‘刚果’、‘尼罗河’、‘大’、‘天空’、‘阴影’、‘鼓’、‘太阳’或者‘过去’。其它一些拥有的词语包括‘游击队’、‘没有时间的概念’、‘原生态’以及‘部落’。注意,‘人们’说的是那些不是黑人的非洲人,而‘人民’则说的是黑人。”
非虚构的使命
这一年的非虚构市场因为死亡而颇为可圈可点。先是历史学家托尼·朱德终于屈服于肌肉萎缩症,他的自传《记忆的农舍》(The Memories’ Chalet)也许是本年度最值得收藏的作品——《乔布斯传》除外。之后,克里斯多夫·希钦斯的突然过世也带来了如他本人的一本散文集《有争议的》。另一部受关注的非虚构作品也与死亡有关,著名小说家乔安·迪迪恩(Joan Didion)的《忧郁夜晚》(Blue Nights)悼念她几年前死去的女儿,这个好莱坞上流女作家在这本书里回归寡淡的忧伤,进行着与女儿有关的自我检讨。
对于文学爱好者,乔纳森·勒瑟姆(Jonathan Lethem)的散文集《影响的极乐》(The Ecstasy of Influence)是本不能忽略的作品。可以说,勒瑟姆是当今最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小说家,他对波拉尼奥的热爱与他们共同的书店经验有关。勒瑟姆和波拉尼奥一样都是为自己而做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多半是逃了学,从马路上一头栽进书店的。波拉尼奥偷书,勒瑟姆则做了很多年的小书店员工。《影响的极乐》里大部分的文章都与阅读经历有关,真诚而感人,能够揪起所有为阅读而极乐的人的小心脏。
2011年另一本少见的有趣书是浑身充满戏剧性的法国小说家米歇尔·维勒贝克与法国哲学家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evi)的吵架邮件结集成的《公敌》(Public Enemies)。与法国哲学的黄金时代时隔多个十年,法国人的思考仍然极度的形而上又极端地抓住重点。两人吵架的起因是维勒贝克写到自己父亲在二战时期看到几个法国士兵杀死了一个纳粹,而他父亲总结道“我觉得那没什么意思”,而维勒贝克对此表示同意。列维对维勒贝克的政治不正确开始发动攻击,而维勒贝克一上来就告诉列维像他们这样的人基本都是值得鄙夷的,维勒贝克坦承自己种族歧视、虚无主义、反动、憎恨女性,而其实大部分人都如此,而列维则认为这种自暴自弃、虚化道德观正是文学应该避免的道德腐败——“我憎恨这种忧郁主义,虽然它正变成这个时代的属性”。两人的争辩充满火药味,很像中国微博上公知的掐架,却高级、深刻了许多倍。
非虚构写作变得越来越吸引人,就连最严肃的小说家,也纷纷隔年出版一些散文,你会发现在他们的散文里他们放得更开,情感更真实,意见也更直接。也许非虚构写作,在一个小说沦陷的年代是有使命的。
展望2012
2012年,非洲写作凯恩奖的新作品集将出版,有机会看到鲜有发表的非洲文学的一些新方向。罗恩·拉什(Ron Rash)的新作《河湾》(The Cove)可能是2012年上半年最值得关注的小说作品。内森·英格兰德(Nathan Englander)继弗朗西恩·普洛斯以后也要写一本关于写《安妮日记》的安妮·弗兰克的书,名叫《当我们讨论安妮·弗兰克的时候我们讨论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Anne Frank),这个犹太身份的问题似乎永垂不朽,而约翰·欧文(John Irving)的新书《合体》(In One Person)写的则是一个1980年代雌雄同体人的故事,进一步把身份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当然,这是个把炒作文学化,把文学符号化的年代,所以我们对明年文坛的叙事几乎毫不知情也并不奇怪。谁会是赢家是个愚蠢的问题,但2011年,美国的Borders连锁书店倒了,Kindle又出了新的版本,赚了很多钱,虽然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与用什么看几乎完全没有关系。2012年,可以肯定的是又有无数书店会关门,又有无数年轻写作班毕业生一头栽进文学圈的游戏,只能说也许的是一个非洲人会得诺贝尔奖,也许明年布克奖的短名单会更看不懂,而有可能的是,2012与2011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这是一个你越来越分不清楚畅销小说和文学小说之间区别的年代,这一年,看似默默无闻一炮走红的查德·哈巴克(Chad Harbach)靠一本讲棒球的小说在文学界打了个大满贯,但你知不知道这个哈佛和弗吉尼亚大学写作班毕业的人90年代开始就已经混迹文学圈?你又知不知道《外野艺术》(The Art of Fielding),这本被屡屡与大卫·福斯特·瓦莱士相比的新时代文学大作出自于Litte,Brown这样一个出畅销小说尤其是青春畅销小说的出版社?(哈巴克与大卫·福斯特·瓦莱士的相似之处大约仅限于前者喜爱后者)。圈子的力量是伟大的,而2011年的欧美文坛离不开查德·哈巴克,或者25岁来自南斯拉夫的天才少女提亚·奥布莱特(Tea Obrect),或者史蒂芬·金更为文学的尝试,又或者晚于很多市场一年多才上市的英文版《1Q84》——这最后一条,我总觉得是个营销阴谋,如果《1Q84》不是在2011年上市,这个依赖于名誉大过任何一切的市场在这一年简直要陷入一种尴尬的真空。如果你仔细看,整个欧洲与美国已经找不出多少妇孺皆知的大牌高产小说家,可悲的是仅有的那几个——保罗·奥斯特、乔纳森·弗兰岑或者米兰·昆德拉,都直接跳过了2011。
没有大师的年代
不要问下一个小说大师是谁。这个人不存在。好几年来,终于有一个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得了诺贝尔奖,但诗歌已经有如僵尸,真正的小说离得也不太远。2011年,最受瞩目的作品是布克奖得主朱利安·巴恩斯的《一种尾声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这本书短得惊人,只有150页。在所有巴恩斯的作品里《一种尾声的感觉》完全排不上号,但它正是今年各国书店的头牌。《一种尾声的感觉》的语言当然是巴恩斯的精致,故事却实在说不上新鲜——主人公儿时的朋友自杀了,使得他不得不面对一段早已遗忘的过去。读这本小说,有时候你会发现浪漫主义电影的桥段,比如一个数学公式里镶嵌着四个朋友的名字。“有积累。有责任。但除此以外还有不安。还有很多的不安。”这样多愁善感的句子多过了巴恩斯在《福楼拜的鹦鹉》里那种具有更多层次感的机智与知识分子的敏锐。
巴恩斯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英国作家,他时而是个文化精英时而又贴近群众的泪点或者笑点——一众当红英国作家走得都是这样的路线,从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到杰夫·戴尔(Geoff Dyer),他们讲的总是小生活的故事,语言总是精致优雅又繁复罗嗦,格局之小和这个时代的文学局面可以说是相得益彰。这是个不需要大部头也没有大师的年代,写作是种工作般的行为,它不超越任何东西。每一年的布克奖名单总是招来很多关注,年复一年,这种关注越来越失去意义。你既找不到文学的新尝试,也看不到任何除了讲一个故事以外的意义。今年的布克奖,除了得奖的巴恩斯以外,进入短名单的作品题材让人摸不着头脑,老派女作家卡罗尔·波尔茨(Carol Birch)的《贾马尔奇的动物收藏》(Jamarch’s Menagerie)讲的是个男孩遭遇老虎的故事,黑人女作家艾斯·伊杜格言(Esi Edugyan)的处女座《半血缘布鲁斯》讲的当然是个黑人在二战时期的故事。英国小说总有那么点自恋的气质,好像故事要追求越小越偏越不当代越好。唯一值得关注的反而是A·D·米勒(A.D.Miller)的《雪花》(Snowdrops),这个《经济学人》驻俄罗斯记者的小说处女座把视野放到了新的俄罗斯,叙事里有种新闻写作的紧张感,而不是传统英国小说贵族式的敏感与慵懒。
再顺着文学奖寻找下一个大师是件不靠谱的事情,但欧美文坛从来是个爬名誉阶梯的地方。这是一个连已经故去的斯蒂格·拉尔森都必须被复制的年代——今年北欧悬疑作家仍然走在光明大道上,前有挪威的乔·内斯波(Jo Nesbo),后有芬兰的贾尔克·斯皮拉(Jarkko Sipila),谁能想到“斯堪地纳维亚犯罪小说”也能成为一个“类型”,更有趣的是这批北欧作家有个共同的特质,他们似乎都与斯蒂格·拉尔森一样,曾经或者仍然在做记者。可怕的当然不是类型小说的批量复制,而是类型小说对正统文学的侵入。查德·哈巴克的忽然走红是个奇怪的现象,这一切机缘巧合贴得太天衣无缝,正是美国流行的橄榄球电视剧《周五夜晚》(Friday Night Lights)要闭幕的时候,就连电视都需要下一个德克萨斯体育爱情故事。这个时候我们迎来了今年最受宠的一个名字,他受到的追捧让人难以理解,这本书里充满了棒球术语,任何一个缺乏棒球基本知识的人都无法读完前五页而不被类似“短停”(shortstop)之类的词语难倒,更不用说《外野艺术》这个名字在小说里是本棒球秘笈。
查德·哈巴克像一个写作班里很多的、热爱写作更热爱体育的普通男青年,他碰巧却有强大的人脉。这个纽约嬉皮文学杂志《N+1》的编辑不知在布鲁克林的酒吧里交了多少出版界和媒体界的朋友,使得这场炒作几乎具有历史意义。“圈内人”捧出来的畅销书作者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无关于写作的质量,而是把明明是类型小说的《外野艺术》在文学境界上彻底提高了一个档次。它成为了《纽约时报》等各大主流媒体的年度十佳小说之一。它被拿来和过去的男性主义作者(Macho Writer),比如瓦莱士或者海明威相提并论——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海明威固然是斗牛爱好者,对此费尽笔墨,但他从来没有局限于在斗牛里看斗牛。
2011年,整个欧美文坛没有一部让所有人惊艳的作品。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又一本遗作《第三帝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本来就不应该被发表。从《巴黎评论》连载的一开始,所有人就都意识到这是个失败的小说,以至于在连载的第二期上《巴黎评论》不得不在封面上印了“这部分情节更扑朔迷离”这样怪异的宣传语。杰弗瑞·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虽然个性乖张,却爬不出准一流作家的行列,《婚姻情节》(The Marriage Plot)中规中矩乏善可陈,讲得是一个大学毕业之后成长的故事。村上春树的《1Q84》固然让欧美读者有所期待,却谈不上是村上春树最好的作品。2011年值得尊敬的小说家是史蒂芬·金,《11/22/63》反而是本真正的文学作品,用一种非常聪明巧妙的方式牵连了出了一个有关刺杀肯尼迪凶手的故事。
当然,这一年也不是没有一些精彩,尼克尔森·贝克(Nicholson Baker)的《洞之屋》(House of Holes)荒诞不经,口味重而具有颠覆性。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重版的小长篇《火车梦》(Train Dreams)写的是美国大西部开发时期的火车旅程,与他以往的作品一样具有空灵的毁灭感。高产的弗朗西恩·普洛斯(Francine Prose)语言依然清脆而黑暗,《我的美国新生活》(My New American Life)里反讽和调侃玩得恰到好处。
视野望向哪片大陆
欧美文学界缺乏新鲜的刺激并不是新鲜事,一个波拉尼奥掀起如此大的浪潮并非偶然,因为在欧美,像小冯内古特或者约翰·厄普代克这样的“作家中的作家”已经越来越少,如今也只有米歇尔·维勒贝克对得起这样的名誉。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商不得不把视野越来越多得望向远处。翻译小说曾经在欧美毫无市场可言,如今像村上春树这样的外国作家早已占据了头牌位置,并且出版商正挖空心思地发掘更多的斯蒂格·拉尔森或者波拉尼奥,如今年轻作家的阵营里非英语国家出生的已经超过了半数。
实在不行,还有蒂亚·奥布莱特(Tea Obrect)这样的半外国作家。年轻的奥布莱特文字里有种小公主的气质,它细致、耐心、富有真情实感,甚至有时单纯无辜,但很奇怪,这本2011年除了《外野艺术》以外又一本被广为推崇的小说《虎妻》(The Tiger’s Wife)有的时候读起来好像一本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巴尔干文化指南。差不多的题材,曾经的《恶童三部曲》造诣要高得多,在欧美的反映却几乎从未那么热烈。当然,欧美文坛需要这些东西,问题是,应该往世界的哪里看?
亚洲文学在欧美近几年的表现非常之差是个不争的事实。几乎没有一个除了村上春树以外的亚洲作家找到任何一点的突破。这里面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翻译的困难,而是市场的不对等。拿中国来说,欧美文坛要找的是比郭小橹质量更高也更有市场潜力的又一个郭小橹,富有西方意义上的冲击力和政治性(女性主义、种族、压迫等等),而中国愿意推的却是文学性很强,题材又十分乡土,让英语读者感到隔阂生硬的50、60后作家。去年《格兰塔》杂志出了本西班牙语小说特刊,今年《格兰塔》在讨论的是自2005年以后的又一本非洲特刊。非洲是2011的关键词。另一部被广泛追捧的处女座小说是《开放城市》(Open City),来自尼日利亚出生的特于·科尔(Teju Cole),写的是曼哈顿,当然也融入了非洲的记忆。在南美、亚洲和中东各自被注视良久以后,非洲是仅剩的一块文学处女地。但真正出自非洲的那个小说新星,在库切之后后继无人,且属于非洲黑人的文学离良好的发展越来越远。
另一本非洲关注的作品是肯尼亚黑人小说家Binyavanga Wainaina的自传体小说《有一天我会写这个地方》(One Day I Will Write About This Place),这个相对年轻的作家是近年文学圈非洲声音的最大代表。他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打油诗,叫《怎样写非洲》:“永远在标题里写‘非洲’或者‘黑暗’或者‘丛林’。小标题可以包括‘赞自巴尔’、‘马萨伊’、‘祖鲁’、‘赞贝兹’、‘刚果’、‘尼罗河’、‘大’、‘天空’、‘阴影’、‘鼓’、‘太阳’或者‘过去’。其它一些拥有的词语包括‘游击队’、‘没有时间的概念’、‘原生态’以及‘部落’。注意,‘人们’说的是那些不是黑人的非洲人,而‘人民’则说的是黑人。”
非虚构的使命
这一年的非虚构市场因为死亡而颇为可圈可点。先是历史学家托尼·朱德终于屈服于肌肉萎缩症,他的自传《记忆的农舍》(The Memories’ Chalet)也许是本年度最值得收藏的作品——《乔布斯传》除外。之后,克里斯多夫·希钦斯的突然过世也带来了如他本人的一本散文集《有争议的》。另一部受关注的非虚构作品也与死亡有关,著名小说家乔安·迪迪恩(Joan Didion)的《忧郁夜晚》(Blue Nights)悼念她几年前死去的女儿,这个好莱坞上流女作家在这本书里回归寡淡的忧伤,进行着与女儿有关的自我检讨。
对于文学爱好者,乔纳森·勒瑟姆(Jonathan Lethem)的散文集《影响的极乐》(The Ecstasy of Influence)是本不能忽略的作品。可以说,勒瑟姆是当今最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小说家,他对波拉尼奥的热爱与他们共同的书店经验有关。勒瑟姆和波拉尼奥一样都是为自己而做的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多半是逃了学,从马路上一头栽进书店的。波拉尼奥偷书,勒瑟姆则做了很多年的小书店员工。《影响的极乐》里大部分的文章都与阅读经历有关,真诚而感人,能够揪起所有为阅读而极乐的人的小心脏。
2011年另一本少见的有趣书是浑身充满戏剧性的法国小说家米歇尔·维勒贝克与法国哲学家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evi)的吵架邮件结集成的《公敌》(Public Enemies)。与法国哲学的黄金时代时隔多个十年,法国人的思考仍然极度的形而上又极端地抓住重点。两人吵架的起因是维勒贝克写到自己父亲在二战时期看到几个法国士兵杀死了一个纳粹,而他父亲总结道“我觉得那没什么意思”,而维勒贝克对此表示同意。列维对维勒贝克的政治不正确开始发动攻击,而维勒贝克一上来就告诉列维像他们这样的人基本都是值得鄙夷的,维勒贝克坦承自己种族歧视、虚无主义、反动、憎恨女性,而其实大部分人都如此,而列维则认为这种自暴自弃、虚化道德观正是文学应该避免的道德腐败——“我憎恨这种忧郁主义,虽然它正变成这个时代的属性”。两人的争辩充满火药味,很像中国微博上公知的掐架,却高级、深刻了许多倍。
非虚构写作变得越来越吸引人,就连最严肃的小说家,也纷纷隔年出版一些散文,你会发现在他们的散文里他们放得更开,情感更真实,意见也更直接。也许非虚构写作,在一个小说沦陷的年代是有使命的。
展望2012
2012年,非洲写作凯恩奖的新作品集将出版,有机会看到鲜有发表的非洲文学的一些新方向。罗恩·拉什(Ron Rash)的新作《河湾》(The Cove)可能是2012年上半年最值得关注的小说作品。内森·英格兰德(Nathan Englander)继弗朗西恩·普洛斯以后也要写一本关于写《安妮日记》的安妮·弗兰克的书,名叫《当我们讨论安妮·弗兰克的时候我们讨论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Anne Frank),这个犹太身份的问题似乎永垂不朽,而约翰·欧文(John Irving)的新书《合体》(In One Person)写的则是一个1980年代雌雄同体人的故事,进一步把身份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当然,这是个把炒作文学化,把文学符号化的年代,所以我们对明年文坛的叙事几乎毫不知情也并不奇怪。谁会是赢家是个愚蠢的问题,但2011年,美国的Borders连锁书店倒了,Kindle又出了新的版本,赚了很多钱,虽然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与用什么看几乎完全没有关系。2012年,可以肯定的是又有无数书店会关门,又有无数年轻写作班毕业生一头栽进文学圈的游戏,只能说也许的是一个非洲人会得诺贝尔奖,也许明年布克奖的短名单会更看不懂,而有可能的是,2012与2011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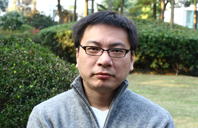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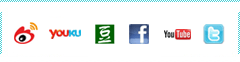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