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东东(1961— ),自由作家,诗人。出生并长期生活于上海。1981年开始写作,是诗刊《作品》(1982-1984)、《倾向》(1988-1991)和《南方诗志》(1992-1993)的主要编者。曾任海外文学人文杂志《倾向》的诗歌编辑(1994-1997)。自2004年以来,参与策划和操办“三月三”诗会多届。作品包括诗集《夏之书·解禁书》《导游图》和诗文本《流水》等。与诗人张耳合作编选英汉对照本中国当代诗选 Another Kind of Nation: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Talisman House, 2007),与诗人张枣合作编选《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Sze-Lorrain]
为什么选择诗作为一种表达方式?你的写作是否有一个“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
[陈东东]
普罗泰戈拉(Πρωταγόρας)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的有一层意思,我想,是要表明人的一切思想、见识和行为并没有可能跳出这句话的限定。语言既是所谓尺度,也是所谓人。因为语言,世界成为人的表达;因为语言,人成为对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世界的表达。那么,为什么表达就无需多言——表达恰是我们这个可以将语言作为其定义的种类的性质。而为什么选择用诗来表达,似乎也一样能够自明。
诗性本质于语言,并且造就语言最初的形态;诗性是为人性最重要的成份。我甚至认为,诗(诗意)正应该是人类的目标/目的。到了青春期,我估计,每个人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活跃着一个诗人。就像在某个幼龄(通常是断奶后不久),人获得了语言能力,学会了说话;伴随着一个人的第二次生长发育高峰、性成熟和恋爱求偶的需要,人也往往会对语言又有一次热切的关注,而那正是以诗的方式去关注表达自身,语言自身。作为一种表达方式的诗,总是会倾向于对表达方式的表达;诗去体现并让人意识到语言之为语言的所以然,那个“存在的尺度”和“不存在的尺度”的所以然。我想说的是,因为语言,诗的写作跟人的存在有着天然的关联。
人的存在朝向诗,诗显现人的存在。那么,能否说,是诗选择了人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尽管,看起来,像是人去选择诗。而在我刚提笔写诗的时候,这种必然性,却是更多地扮作偶然恰巧,在我身上开始工作的。1981年,我20岁,正在大学读书。如我曾经提及的,朝着现代社会转型的当时中国的时代风云、文化气象,我所在大学中文系的氛围,我正当青春的精神面貌,再加上跟我私交甚好的同学和朋友有几个恰是不错的诗人,对我构成了影响……这些方面,好像都催促我去选择诗,去成为一个诗人。在另外的场合,我回忆起不期然读到李野光翻译的希腊诗人埃利蒂斯(Οδυσσέας
Ελύτης)的一首长诗对我的激发,我最初的诗行,正像是对那首长诗的回应。那时候,诗被我定义为“灵魂革命、绝对信仰、肉体音乐、精神历险和真正的生活”。
写诗多年后,我还曾这样表述:“我的想象常常因一种无词之意味而启动,终于穿越一重或多重词之境,差强人意地抵及一首诗。当我自问为什么选择诗的时候,我不止一次设想,很可能,诗只是作为音乐的替代品被我迫不得已地拣起来应用。那像是因为我不会音乐,退而求其次。实际上呢,萦回我心间的节奏、语调和境界之表达,惟有以诗的方式,才更能曲尽其朦胧或明澈、幽微与晓畅、细碎及旷放、俯仰高低和张驰缓急……然而,要是我诗的航船有它自己的方向和目的地,诗的罗盘指针,则总是被音乐的磁极所牵引。音乐像是个绝对和终极,高于进行时态的写作的诗,而成为所谓理想的诗。这种理想的诗,我猜想,要用异于日常话语的纯粹语言来演奏……那纯粹语言并非日常话语在某一方面(譬如说,语义)的减缩和消除,相反,它是对日常话语的扩充和光大,是语言的各个重要侧面同时被照亮,并得以展现。”
音乐被我目作最高级别的内在生活,或许,音乐可以是企图超越语言尺度的人类激情。只不过,音乐也还得用语言来测量,还得要用诗不断地予以定义。当我用上面这段话回答“为什么选择诗”的时候,我想我已经说出了我写作的“存在”的理由。如果“语言是存在之家”,那么,我想要用我的写作语言去向往某种存在,去超越某种存在,去回望某种存在。而我用语言塑造的诗,正塑造我的存在。
[Sze-Lorrain]
你的诗所抵达的意象和想象,看起来似乎直接回应、沿袭了中国传统。作为一个当代诗人,一个公认有自己独特文体风格的诗人,这是你在有意识地创造“永恒”吗?
[陈东东]
在当代中国,用汉语写诗,你还得进行一次选择:旧诗还是新诗?
我从未去填写旧诗词,一开始写的就是新诗。新诗的语言是现代汉语,新诗也被称之为现代汉诗。当这种新诗出现的时候(那是在将近一百年前),我认为,它是以反向于旧诗来分辨和确立自我身份的。新诗的自我依据,却也以反向的方式有赖于包括旧诗、以旧诗为一大表征的传统。可以说,新诗力图使自己成为一棵生长于传统反面的未来之树。这棵未来之树一向充分吸收着现代(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不妨径直就是西方)的阳光雨露,然而它的根须却伸进传统,尽管是反向地伸进;新诗跟在另一个向度挺立着的那棵旧诗的往昔之树,其实共用着中国传统的土壤。并且,我相信,新诗愈朝着未来的时空长大,其根须也势必愈深入传统,纠缠甚至接通粗壮盘绕着的旧诗和别的往昔之树的根须。但这种纠缠甚至接通,我想,不应该也不会造成新诗这棵未来之树生长向度的改变。因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纠缠甚至接通都来自反向。
选择新诗,对我来说,也就大概地选择了对待传统的态度。它首先是一种语言态度——现代汉语刚刚被用作新诗语言的当初,语言态度几乎成了革命还是守成传统的表态——而语言态度的不同,的确会造成丈量测算我们存在其间的这个世界(传统正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单位、角度、方式等等的不同。我愿意认定,现代汉语之“现代”,正有着自己为自己制定规范的现代性品质,而这也是现代汉诗之所以“现代”的一种品质。这品质不同于旧诗的某一端在于,它对它曾经反向依存的传统之定义,来自无数个瞬间聚起的无数个现在,来自无数个瞬间将至的无数个未来。
现在和未来,也成为我的有些诗作“所抵达的意象和想象,看起来似乎直接回应、沿袭了中国传统”的出发点。这些意象和想象以新诗的方式、以现代汉语呈现,我所考虑的,不是因它们而创造“永恒”,而是去从新诗的出生/出身所给出的戏剧化的反向观照它们,去从新诗的反向,辨析、解释、清算和重估中国传统。
[Sze-Lorrain]
能更多说说这种和你写作有关的文体特征吗,以及它们是如何演变发展起来的?
[陈东东]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辨体”理论,譬如,汉末魏晋文学和文体自觉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就把诗赋的文体特征概括为“丽”(有别于奏议的“雅”,书论的“理”和铭诔的“实”)。它一般性地界定了诗这种文体和它的语言风格。包括曹丕在内的中国古代文论普遍的、对于诗的一般性要求,再加上主要来自阅读古典诗词的对于诗的一般性印象,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是形成我有关诗的一般性想象的重要依据。而我刚开始的一个写作动机,则由于我对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生产的那么多诗作的失望——它们大大低于我的有关诗的一般性想象——“当我意识到……我是个无可倾听的钟子期时,我便要试着做一回伯牙”,我曾这样回忆,“我想要把我所想象的诗之样态提供出来,以自制的模范作品说:‘这才是诗歌’!”这种当初显得狂妄的朴素动机,后来还是常常成为我写作的动机之一种。这样的一种动机,我想,的确会推动我去成为“一个有自己独特文体风格的诗人”。
一开始,这种针对丑陋荒谬的文革暴力词语、党国言说模式、红色话语系统和政治抒情诗风的动机,迫切地要让诗人去发明他个人的文体语言,以抵御和抗议集体和极权性质的众口一辞。那种往往借用乃至强奸工农兵群众、广大劳动人民名义的众口一辞,常常炫耀其自以为是的简陋、粗鄙和口水化风格。它跟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倡导的朝“下里巴人”的倾斜有关,也跟新诗发生前后(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所倡导的平易、通俗的白话有关。与之相反,我所期望的是自尊和被尊敬的更具中文性和音乐性的文体语言,这种作为新诗语言的现代汉语,具有书面化的雅语性质。不过,我所谓“书面化的雅语性质”不指向文言,或许,称之为我自己的“拟似口语”的写作语言会比较确切。
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个人原因是,我的写作语言很难从我日常使用的俗语方言,我严格意义上的母语——上海话那里得到多少有效的援助。上海话的不能被标准的和哪怕不怎么标准的书面汉语接纳,差不多杜绝了我将自己的口语资源应用于写作语言的可能性,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我去创造我自己书面化的、雅语性质的文体语言。这种文体语言的资源是文学化的古典哲学、宗教、历史著作,笔记、小说、演义和戏曲,当然,尤其是伟大的中国古诗词。不过,对这些资源的获取常常是反向式的,原因我已在前面提及——我想要有所建树的,属于现代汉诗这棵未来之树。翻译语言也是我所征用的重要资源——翻译,使得汉语有了一种被引向外语幻境的镜像深度,并且就算镜子并无凹凸不平,镜子还是在左右和前后两方面改变了事物的向度;可以说,现代汉语的形成跟翻译语言对汉语的镜像运用大有关系——而我对翻译语言的征用,则企图用这种对古老的汉语现实而言近乎杜撰的镜像语言去映照之,有如月亮对夜间事物的映照。
我想,我的方式正是我所理解的现代汉语的方式。现代汉语在它的三个来源——口语方言、古汉语和翻译语言的对话和砥砺中成长和成熟,我的文体语言的中文性依据,亦在这样的对话和砥砺间。要是文体语言有个什么配方的话,那么,像是为了补偿我文体语言的配方里甚少我在上海街道里弄的日常场景说话的声音腔调,我假想了一种或数种可能的、也许的、仿佛的“拟似口语”。它们对于我个人而言已经不陌生,它们差不多是我内心自白和梦里依稀的日常语言。这种可以被书写下来的“拟似口语”,被我大剂量地配方进我的文体语言。并且,“拟似口语”——一方面不去临摹仿写、而是超越口语方言,一方面又灵活地逃脱标准书面语的死板陈规、成语滥调——是我文体语言的方向。运用这种书面化的、雅语性质的“拟似口语”,我检讨进而抵制新诗写作的历史和现状里那貌似革命性的“我手写我口”。在此,我想起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一句话:“无法对写作的方式跟说话的方式一样的作家感到兴奋。”
用不同于平常说话方式的语言去写作,密切相关于对文体语言音乐性的注重和追求。在这方面,我认为,用崭新的现代汉语写下的新诗,仍然应该跟旧诗传统形成那种反向超越的关系。构成我文体语言的音乐性,并不走在许多新诗写作者曾为之努力的新格律之路上。对新诗格律化的那些构想,均以传统旧诗的格律规则为榜样和参照。然而,传统旧诗走上格律化的道路,缘于它以古汉语作为写作语言。而新诗——现代汉诗使用的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作为不同于古汉语的另一种汉语,跟现代汉诗以反向于古诗一般基础为立足点相一致,也跟古汉语呈一种反向的关系。当古汉语已经充足圆满、固步不前、仅属于往昔,现代汉语却翻转过来,不要拘束、满含可能性、用未来追认着它的此刻。由这种语言成就的现代汉诗,自由度可谓相得益彰。新诗——现代汉诗的本性,自当拒斥制服般的格式和镣铐一样给自己戴上的铁律。所以,我不认为应该为现代汉诗制订一份和数份格律表单,那种降低难度的填空式写作(可能)带来的诗歌程式化甚至制度化,会跟现代汉诗自由不羁的灵魂格格不入。实际上,不考虑现代汉语的特性、仿照旧诗词或外国诗律裁制的紧身衣诗格,不会合体于现代汉诗;在现代汉诗并无内在需求的情况下为其杜撰的无律可言之诗格,则几乎连揠苗助长都算不上。
我对我的文体语言之音乐性的把握,是建立在确认新诗——现代汉诗的不会(不该)走上所谓新格律道路的基础上的。然而,这样的确认,却并不以为现代汉诗真的就可以自由到散文化了事——现代汉诗就像用任何语言写下的任何样式的诗一样,试图远离散文。在我看来,新诗——现代汉诗的自由体和自由化不等于散文体和散文化,它那诗的规定性恳求着属于现代汉语的节奏和音乐。我看到,现代汉诗与众不同的节奏和音乐是如此与众不同——它要使每一首诗仅是这首诗本身,每一首诗仅是由这首诗形成的那么一种诗——它最大限度地避免诗人声音的类似化和类型化。也就是说,你每写一首新诗,就要走一程新路,来一次新历险;你的每一首新诗在语调、节拍、形式、结构、布局等方面,都应该是一次新的抵达。由于没有可以称之为“他律”的外在诗律,现代汉诗的写作更具挑战性和创造性,它需要诗的高度“自律”——现代汉诗不是自由诗,而是自律诗。
一般而言,自律需要节奏的自觉。因为不依靠(没有)外在规定性,你得凭呼吸和倾听去发明自己写作语言的诗之音乐,这牵涉到写作中的一系列调整,语气、语调和语速,押韵、藏韵和拆韵,旋律、复沓和顿挫,折行、换行和空行……这是每个诗人都得学会的手艺,并无稀奇。要之,自律的自觉带给我“因地制宜”的写作观念:每一首诗的,仅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音乐性之依据,正在于这首诗的起源和发生学内部,就像每一首诗的文体风格来自这首诗的起源和发生学内部。当然,这种起源和发生学,会上追新诗和现代汉语的起源和发生学,会上追新诗和现代汉语与之反向而同一传统的旧诗词和古汉语的起源和发生学。
那么,在用更具中文性和音乐性的具有书面化的雅语性质的“拟似口语”表述我的文体特征的同时,我还想说,我期望“因地制宜”才是我的文体特征。所以,我很少有意识地以强化的方式去演变发展我的文体风格,演变发展于我仿佛是无意识的,变化由于“因地制宜”,由于我对不同诗思和诗意的关切。
[Sze-Lorrain]
你认为你的一些文化/特定历史的诗,可能会因为环境的陌生性导致疏远读者吗?
[陈东东]
我还是引用苏珊·桑塔格吧。她说:“我不考虑读者,只考虑文学。”我强烈认同她的这一态度。那是我关于写作的首要态度。我不知道我的某些诗作会不会疏远读者,我所想的是,我的写作总是能够去成就诗。
或许我的某种题材的诗会让有些读者感到陌生,不过即使在处理某些特定主题的同时,我仍然要把诗本身作为诗的主题——诗的写作正该如此:一方面拓展着诗的外延,一方面又去深究诗的内核——那么,就算你写的是所谓反诗,你也得把它当纯诗来写。所以,要是读者希望读到的是诗,从处理特定题材、特定主题的作品里,也还是希望读到的是诗,我想,它们就并不真的会疏远诗的读者。
[Sze-Lorrain]
桑塔格对“永远不要考虑读者,只考虑文学”的意见在别人看来可能是无视群体的,自我中心的。你的想法呢?
[陈东东]
我想,桑塔格的文学定义里应该已经包含了读者,正如人们一般而言的文学概念里,自有关照读者的方面。
桑塔格的说法看似绝决,仿佛无视读者群体,实则,在我看来,正好是以更专注地服务于文学的态度,维护了文学的读者的利益。文学的读者因为文学而存在,反之当然也说得过去,然而,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若无文学之皮,文学的读者又会在哪里?过多考虑读者的写作很可能付出的是牺牲文学的代价。专心于文学,才可能对得起读者。
[Sze-Lorrain]
那你如何定义“可诣性”(accessibility)?用一种易懂的语言和风格来进行写作,是否属于你的美学纲领的一部分?为什么?
[陈东东]
“accessibility”译成汉语,大概为“便于接近;容易获得”,有着“可接近性”“可访问性”“可抵达性”等意涵,译作“可诣性”,应该不错。我想,你问的是我对语言和诗的“可诣性”的看法:这包括对透过诗的语言去抵及世界真实的这么一种写作可能性的看法,和对透过诗的语言去明确作者真意的阅读可能性的看法。对“可诣性”的定义,正该包括这两个方面。可是语言不仅是通道,更是樊篱,它除了让人接近对世界的认知,而又阻隔人对世界的洞察——语言对世界选择、计量、分割、重组、包装……语言并不让人抵达世界真实,而是建构语言的世界。我认为在读者去抵达写作者真意的路上,诗的语言也一样既是通道又是樊篱,诗的语言在读者那里,建构的永远是读者读到的诗,而非作者想写的诗。于是,如果我来定义“可诣性”,就会在绝对的层面上指出“可诣性”的不可能性。朦胧,含混,晦涩,相对于透明,清晰,晓畅,是更本质的诗的表达。
我知道有人企图用所谓“易懂的语言和风格来进行写作”。且不说这种企图是否真的能达成,是否在达成的企图里反而丢失了最起码的诗性;在我看来,追求易懂的语言和风格,显然会造成表达的简陋和单薄。须知,简洁和单纯不同于简陋和单薄,简洁和单纯一定不属于易懂的语言和风格。譬如李白的《静夜思》,那种由简洁和单纯造成的委婉,含畜,丰富,耐人回味,其实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易懂。尽管诗的“因地制宜”也许在某种特定的情形里未必不可能运用“易懂的语言和风格来进行写作”,但通常我厌弃用“易懂的语言和风格来进行写作”。
我说过,我的写作语言检讨新诗的出生/出身里的“我手写我口”。这种“文学革命” 设计的倾向于直白易懂的语言方案,其实相悖于革命性的新诗来到朝着现代化艰难转型的古老中国的必要性。新诗的必要性在于,需得有一种全新的能够说出人(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的复杂感受、复杂认知、复杂判断和复杂表达的语言和诗。新诗——用现代汉语写下的现代汉诗,尽管反向于旧诗词,却一定不会比过去时代的旧诗词在语言和风格上来得易懂,只是,新诗那奇异的复杂所收获的奇异的茂盛,也将出于旧诗词的反向。我甚至认为,那种被目作晦涩的语言风格之诗,要比追求用所谓“易懂的语言和风格来进行写作”的诗,更多地考虑了“可诣性”。语言风格的晦涩往往出于诗人意欲对现代世界及其心灵的复杂性这一真实情形的深奥转达,那是直白易懂的简陋单薄所无以表述的。
[Sze-Lorrain]
静默——它超越经验的暗示力——在你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诗中发挥着强作用力。你如何摆弄静默的存在和语词间听到的音乐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和平衡?这种静默,为冥想留出的虚拟空间,弹性又有多大?它是否更是一种重量而非速率?
[陈东东]
我把静默也当成诗人发声的一部分,词语音乐的一部分。当然,那是最为特殊的一部分。在我看来,静默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静默既抽象又具体,既是隐喻性的,又是写作时需要认真处理的技术问题。诗人的声音从静默出发,而又归于静默;于是,一首诗除了摆脱静默的动机,又有融入静默的目的。一首诗里的每一个由词语发出的声音(它们构成诗之音乐),都避免不了语义的混羼而无从抵达音乐的纯净;唯有静默,这个最低限度的听不见的声音,不跟语义相捆绑,成为纯净的虚空音乐。它是无限,足够容纳所有的语义。
正是在对静默的如此意识里,我曾把音乐设想为绝对和终极的诗。那么,如果音乐是以词语为材料构成的篇章所无能成就的理想的诗,静默就是以语义的声音构成的诗作的一个可以抵达的绝对和终极。从静默迈步进入诗的发声需要一番新激情、一种新思想、一个新契机;将诗的写作带往静默,更需要一番新激情、一种新思想、一个新契机。
前些日子,我给我那个面对常熟虞山的写作房间起了个名:见山书斋。“见山”之义,来自唐代高僧青原惟信——“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个公案,正可说出静默之于诗的发声。静默或许在我诗的发声以外,却更是我诗的发声的风暴眼——这个比喻,大概能回答你对我提出的静默问题。
[Sze-Lorrain]
在《野寺》一诗里,你以“静观,默想”开头。
初读之下,不妨说这是禅意的关键。事实上,我时常在你的作品中发现佛教的暗流。你是否同意?你是否觉得写作是一种冥想练习(或实践)的形式?
[陈东东]
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但是在我身上,一向持续着对宗教信仰的亲近感,尤其,我有着更多对于佛教的亲近感——也许,反而正是这种亲近感,使得我成不了一名佛教徒。我想,我赞同乃至赞赏佛教对世界和人生的判定,并且,我比佛教绝望——我不认为会有所谓了脱的途径——而这让我在最终极之处认定“意义”的毫无意义。于是,运用语言的诗之写作,就不妨去超越意义,超越语言。这种超越,有一些就跟禅法相通。
在我刚开始写诗的时候,我热衷于阅读禅宗公案和超现实主义作品,我提出过我的写作口号:“禅的超现实”,然而我至今不能为它下一个定义(幸好我没有下什么定义,没有让我的写作受缚于一个什么定义)。《野寺》这首小诗,正是写于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喜欢说:“写作是一种修炼。”它的意思,包含“写作是一种冥想练习(或实践)的形式”;它也跟我将自己的写作比喻为“演奏”有所关联。修炼为了提升境界,我的写作大概也有相似的企图。冥想练习则是典型的修炼方式,它的另一个名称,恰恰是“禅”。以禅法比附诗法,在中国由来已久,我那时候感兴趣的则是中国禅宗“不立文字”对诗的写作的启发。
然而,诗又如何能“不立文字”呢?禅宗公案对诗的提示在于,它并非所谓的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而是给那不可言说的无意义以特殊的言说方式,从而由特殊的言说方式去悟出那不可言说的无意义。它恰恰运用语言的技艺来超越语言和意义,它对语言和意义关注的重点在于,令所呈现的语言和意义成为语言和意义的消失形态。在禅宗公案里我常常看到,“不立文字”的方法,是不把“文字”当成“文字”来“立”或把“文字” 不当成“文字”来“立”。在某个层面上,这也是超现实主义的方法。
冥想改变意识,写作这种冥想练习,从改变对语言的意识开始。我将这种意识的改变朝向音乐——去除意义的词语正是一种声音,附着于词语的意义,也不妨是声音背后的声音。诗人,则是那个练习演奏词语音乐的人……
[Sze-Lorrain]
说起音乐,可否说出几位给你收获或灵感的音乐家?
[陈东东]
我一直没有养成专注地去听音乐的习惯。音乐于我除了是一种理想,常常主要是一种氛围。我听杂七杂八的很多曲子。要是让我说出几位对我的写作有过具体帮助的音乐家,那么,第一位几乎是个无名者——古琴曲《流水》令我构思和写下了诗文本《流水》。这个曲子的曲作者到底是谁,现在没人说得清楚。它的曲本,最早见于朱权的《神奇秘谱》。诗文本《流水》的篇章布局对应于古琴曲《流水》的曲式结构,摹用和发挥其文字谱的语言方式,并以臆写伯牙和钟子期传说作为展开……
巴赫跟莫扎特我曾非常爱听,他们的作品也对我的诗有过很具体的影响。我的有些诗作的对位式写法,受到了巴赫的启发。而我最早的一些诗的节奏,企图仿照从半导体收音机收听到的调频节目里莫扎特某个曲子的节奏。
音乐对我写作的影响,更在比拟的意义层面。早先,在谈论我的写作时,我曾提及演奏,“——演奏,在时光里完成音乐(它是对诗的一个比喻吗),前提是反反复复地练习,去细察、领悟、理解和把握,也许这才是我的写作。……我知道,所有的练习只为了一次真正的演奏。换一种意思稍微不同的说法:真正的演奏只能有一次。……从开始写作到现在已经那么多年……他仍将继续。在某一时刻,他未必意识到,练习被真正的演奏替代。”(《在某一时刻练习被真正的演奏替代》)
[Sze-Lorrain]
光作为一种苏醒的形式——既是语言上的 [例如,“点灯”里的“我灯一样的语言”]
也是精神上的 [“旧地(古鸡鸣寺)”里的“树和天空追随着亮光”]——在你的许多诗中作为反复的主题出现。作为公民和艺术家的诗人可以帮助世界苏醒和寻求真理,对此你有何想法?
[陈东东]
关于光,我还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光也是一种生长的植物,被雨浇淋
入夜后开放成
我们的梦境
(《夏日之光》)
光作为一种苏醒的形式,还应该有梦想的质地。苏醒的,然而把入梦当成其同义词的光,是我对诗的语言和精神的追寻。有一个时期,我要求我的语言具有如此的光感。这缘于一个诗人的内心需要,这的确也跟一个诗人服务于共同体的愿望有关。那么,诗人愿意相信自己可以是一位公民。然而,诗人承担着怎样的为现代社会所需的职责和义务呢? 说实话,我并不认为诗人有能力找到真理——诗并不被用来传达真理,诗也并不适于传达真理,如果,真的有所谓真理的话。
在我看来,诗的产生因为人性中称之为诗性的原素。这种诗性,无异于人性中神性的一面。要是中国古代那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是可信的,那么,这种神性般的诗性也一定存在于跟人道相感应的宇宙天道。天人之际有一个共同的初衷,共同的终极目标的话,我想,那就是诗。我知道我在此说出的绝不是真理,但它的确是一个信念。诗人的存在,为了信念而不是真理。依据这个信念,我认为,世界、生命和人类的发展和生活摹仿着诗。于是,现代社会的公民诗人,其职责和义务,正在于去修复、去重新发现和发明诗情、诗意和诗的语言。
[Sze-Lorrain]
我很好奇:你的作品自传性的程度有多高?你将那个“我”延伸多远,你的“我们”又有多大的弹性?
[陈东东]
可以说,我的作品有着完全的自传性。
尽管我最期望那种作者彻底隐身于作品背后的“无我”的写作,我也的确有意让我的诗有所“非我”,使得最为自我的那个“我”仿佛并不在我的诗作里面,让说出我的诗作的语调不是最为自我的那个“我”的口吻;然而,我知道,它们仍然不可能真正逃离我,不可能真正逃离我的自传性。当我说:“写作是一种修炼”的时候,我大概已经意识到诗人的目标之一是提升和塑造自我,是在诗作里以一个想象之我的形象和姿态来纠正和升华本来面目的我。当然,“写作是一种修炼”也还有一个相反的向度,那就是在诗作里奋力去撕开,去揭示一个面具后面更为真切的我。
不过,一个诗人总是倾向于在其诗作里丰富和完善其自我。大概,一个诗人的意识有多远,这个想象之我就能延伸多远,甚至,这个想象之我会抵达诗人来不及意识到的更远的远方。那个“我”是所谓“另一个我”,匹配于诗这“另一种声音”。
《另一种声音》是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一篇文章的标题,其中他说:“在革命和宗教之间,诗歌是‘另一种声音’。它的声音是‘另一种’,因为这是激情与幻觉的声音,是这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是古老又是今天的声音,是没有日期的古代的声音。分裂与异端的诗歌,清白与邪恶、污染与纯净、空中与地下的诗歌,寺庙的诗歌与街头酒吧的诗歌,唾手可得的诗歌与可望而不可及的诗歌。所有的诗人,在这些或长或短,或被重复或孤立的时刻,只要真正是诗人,就会听到那‘另一种’声音。”
大概,有多少“另一个我”,就会有多少“另一种声音”,反过来说可能更好,有多少“另一种声音”,就会有多少“另一个我”。而这些正可以被写作“我们”。
[Sze-Lorrain]
可否谈谈你的日常生活和多样的职业经历?
[陈东东]
我的经历并不复杂,从出生到现在,除了旅行,就一直生活在上海。可能因为在上海的时间太久,让我有囿于此地的受困感,于是就常常想要逃离。而逃离的方式除了旅行,就是写作了。
我是从读大学时开始写作的,我在课堂上写,因为觉得教室里听到的那些课程都颇为沉闷和无聊,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我逃离那种沉闷和无聊。后来我在学校的教研室里写作,那时候我已经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我的诗稿边上堆着学生们待批改的作文本子,作文题是国家的教育系统统一规定的,不仅无聊而且有害。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情。后来我逃离我不喜欢的教师生涯——我不用再在课堂上讲授那些国家的教育系统统一规定的无聊而且有害的语文课文了——去了一个有着商会性质的机构,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上班。我在那个机构的史料室工作,访问老工商业者,约请他们写回忆录,有时也为他们代笔。同时我在外滩边上一幢大楼里的一间四围都是史料和档案柜的办公室里写作。
1987年,我因为参加北京诗刊社的第七届青春诗会,超出了请假日期没有回史料室上班,被工商联停职一年。这一年,我到上海歌剧院打短工,做《歌剧艺术》杂志社的编辑。1998年,我离开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企图彻底逃离被囿于其中太久的职业生涯。从此我改在自己家里的上午写作。我似乎只能在上午写作。然而我发现我的写作很难养活我自己,于是我又零零碎碎做过一些杂务,譬如参与建立和维持少林寺网站(我在其中负责做内容),少林寺寺刊《禅露》的副主编,《读者导报》的书评编辑,《东方早报》的专栏编辑,一家图书私营公司的策划,台湾一个政经杂志的采访、摄影和撰稿人……这些工作很少需要我去像模像样地上班,我可以灵活地安排时间。现在我没有做什么杂务了,而这样的状态已经有六七年。我的相对固定的收入来源是为报刊撰写专栏的稿酬。
我不是一个勤奋的专栏写作者,常常懒得去写专栏而愿意以虚度去享用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我的日常生活,无非吃饭、喝茶、读书和旅行,当然,少不了恋爱。需要专门一述的是,我的睡眠质量极好,几乎无梦。我很晚睡,很早起来,上午是我的写作时间。
[Sze-Lorrain]
谈及旅行,对于你的诗来说重要性如何?作为一个作家,你是否观察旅行——从精神和身体两方面——作为一种必要形式的错位?
[陈东东]
我想引用许多年前回答香港一份旅行杂志对我提出相关问题时的一段话来回答这个提问:
“在我的生活里,旅行和写作几乎是同构的。写作针对我个人的意义,是对平庸日常的改造和替换。旅行也正是这么一种活动,让它去邂逅神奇。只不过旅行是一种阅读。当然,写作也是阅读,至多不过是人生之旅页边的阅读笔记。那么,所谓写作也就是旅行的副产品。要是我们把人的一生视为一次旅行——时间之旅,那么,可以说,不旅行就没有写作,旅行对写作的影响就这么具有决定性。当然,我们要谈的是空间之旅,它是实际的,而非隐喻意义上的旅行,它对我的诗歌写作也一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谈论那些旅行中的亲历和见闻,对我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丰富和改变……旅行,你会去面对多少未知和意想不到啊!——它们必然影响了我的写作……旅行尽管不是我的全部生活,却是我的另一种生活,那么,要是我的诗并不都是旅行的产物,至少旅行生养了我的另一些诗。这种决定性,已经不是用影响可以讲清楚的。”
[Sze-Lorrain]
上海呢?这城市在你的创作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在什么意义上?
[陈东东]
关于上海以及我跟这座超级都市的关系,我有过好几种表述。最近的一次,在前几天写给《上海画报》的一篇题为《我与上海》的短文里,我把我与上海的关系比作一位旅行者和一个他不再能够在现实里返回,却每每以为可以在由记忆而生的梦境里继续生活其中的旧家;然而那由记忆而生的梦境却甚至把记忆也改变得快要面目全非了。也许,我还可以把我与上海的关系比作我与一位旧情人的关系,尽管我现在仍然还时常见到她,可是关于她我唯有记忆,并且这记忆因为她现在的状况与过去情形之间的反差而一再被歪曲(也可能是修正)。在诗意情感的层面上,上海在我的作品里大概就是这么个角色。我想这实际上无关上海,不过是我对上海的心理投射。
关于上海,我考虑的是它之于中国诗的意义。由于上海是一座如此不同于传统中国的现代都市,一座从西方舶来,而又被对这种舶来之他者的抵制和接纳的合力塑造起来的现代都市,一座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前所未有的现代都市,我认为,那么,当中国诗将上海作为一个抒写对象,一个诗象的时候,甚至当中国诗人在其诗行里写下上海(作为一个意象)的时候,中国诗就有了质的变异。
作为中国曾经的唯一名符其实的国际化和现代化大都市,上海在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现实和历史方面的意义自不待言。有人说上海是百多年来现代中国的一个缩影,然而,置于中国框架里审视上海,其意义更在于那种反差——可以说,相对于古旧传统的价值系统,开埠直到现在,都市上海成长的进程、发展的格局、演变的结构,一直也更是中国的一个现代梦影。或许,摩登(这个词并非英语modern 的译音,而是来自佛经对古印度“摩登伽女”的讲述。至少在上海话里,这个词跟“现代”并不等同),是这种现代梦影的最佳命名。这个以未来的名义强行嵌入时间现在的摩登,被戏剧般地实在化、事件化、物质化、世俗化、观念化、体制化、理想化、美学化直至妖魔化的摩登,有着春梦和噩梦的双重性,有着芜杂迷乱交错的一系列表情的繁复性,有着截然不同于往昔的崭新的诗意和诗象。崭新的上海诗意和诗象强烈而微妙。它们显然可以被看作截然不同于往昔中国的这座大都市带给诗歌的直接影响。诗歌语言和体式的革命,跟这种影响也密不可分。我的作品常常去处理上海题材,我注重于去写所谓的上海之诗,正因为如此吧。我期望我的上海之诗成为打开上海情境的钥匙,透过文字、词语、诗句和篇章,进入某些历史和现实的层面。
[Sze-Lorrain]
涉及到写一首诗的时候,对现状的你而言,什么是危险的?
[陈东东]
很长一个时期,我把不写当成一种危险。不写,要么你缺乏能力把想写的写下来;要么你沦丧了写作的外在条件(比如说失去了自由);要么你没有了写作的欲望冲动;要么,你已经失语。不过,看起来,后三种情况中断或终止了写作者,可以不算是写作的危险;第一种情况,后来我也不把它当成写作的危险了。缺乏能力把想写的写下来,正可以提供磨砺、培养学习、不断尝试、反复实验、无功而返、再去历险……于是,它实则并不是一种不写,而是常常让你想着去写,又准备去写,去考虑写作本身。
比较可怕、称得上危险的,反而是无所阻碍地写。那种太即兴的、太巧妙的、太轻易的、一挥而就的、淹没在才华里的、频频出手的、数量可观的写作,正隐含着(有时已经是明摆着)写作的危机。
最近十年我对所谓“寡作主义”的赞同,我越来越减缓的写作,大概正有着躲避这种危险的用意。滑溜的、驾轻就熟的写作以降底难度和重复自己为代价,二者都意味着对于世界没有新的发现、对于语言没有新的建树、对于写作没有新的向往。这种危险,的确时时出现在你奉献给诗的每一行、每一个字里。如此,要是推到极端,那么,可否说,写一首诗的时候,那个书写的进程是危险的呢?对我而言,诗的写作总是如履薄冰,它的危险,在你下决心去成为一个诗人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了。
英中翻译:陈东飚
Fiona Sze-Lorrain,以英、法、中文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 英文诗集包括《我丧葬的贡多拉》 (My Funeral Gondola) 和《浇月亮》(Water the Moon)。 英译有柏桦、宇向、蓝蓝、张枣、海子⋯⋯ 法国诗人Auxeméry和当代美国诗人Mark Strand 的诗集与作品。目前担任法国独立出版社Vif Éditions与国际文学杂志Cerise Press的联合编辑。也多年从事古筝演奏专业。现居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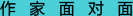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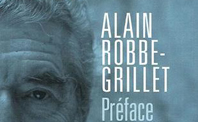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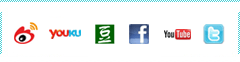

评论